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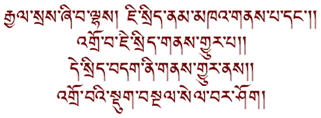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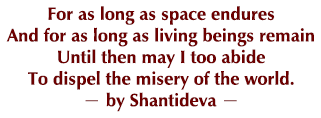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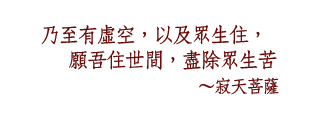 達賴喇嘛格言
你要這樣想:不一定要別人對你有很好的態度,你才需要去尊重、愛護他們。例如,當我們需要雨水時,結果真的下雨了。即使那陣雨並沒有任何想要幫助我們的動機,我們還是會對雨水表現感謝之意。
相關連結
|
藏曆:2152 木蛇年
⌘ 流亡中的自在 ⌘
第十四章:爭取和平
第二支及第三支考察團都在一九八0年五月從印度前往西藏。其中一隊的成員較年輕,另一隊則由教育工作者組成。我希望籍著前者,了解年輕人對西藏情況有何展望;透過後者,則希望知道西藏的年輕一代未來能有什麽樣的展望。
不幸,青年團未能完成查證工作。成群結隊的西藏人夾道歡迎這群離鄉背井的人,在他們面前痛罵中共施政,官方遂指控這些代表挑撥群眾造反;因此以危及『祖國統一』的罪名,將他們逐出西藏。可想而知,我對這種結局很感不悅。中共非但不想『從事實中求取真相』,反倒似乎決心一股腦兒的無視於真相。但至少這次驅逐行動證明,他們還算注意到了西藏人的感受。 第三支代表隊由我的妹妹傑春佩瑪率領,總算獲准留下。這支隊伍於一九八0年十月回到達蘭薩拉,結論明確的指出,雖然過去二十年來,一般教育水準略有改進,但並沒有真正的好處;因為中共似乎認為,認字唯一的作用就是教小孩學習毛澤東思想和寫『自白書』。 整個而言,考察團蒐集的資料,不但完全暴露了中共在西藏的劣性,也顯示西藏人的生活狀況依舊很悲慘。雖然比過去二十年,情況無疑已有改善,但根據中共官方自己的說法,西藏人仍被認為是『落伍、無知、殘酷、野蠻』。 一九八一年,我母親中風,臥床不久便告去世。她畢生(她將近百歲)都很健康,因此臥病在床對她而言是重新的經驗。這代表她第一次得依賴別人。過去我母親一直自己照顧自己。例如,她喜歡早起,但她從不逼僕人為她早起,她早晨自己沏茶,儘管她有個手腕受過傷,行動不是很方便。 她在世的最後一個月,與她同住的天津秋結坦白的問她,孩子之中她最疼誰。我想他覺得自己該當之無愧。但是,她回答是羅桑桑天。我提及這件事是因為當我弟弟告訴我這事時,我也以為她會選中我,但也因為她臨終之前,唯一在場的就是羅桑桑天。我在那之前步行到她的小屋,跟她短暫的見了一面,但大限到時,我卻離家在菩提伽耶。 我一接到消息,就禱告她來世轉生順利。在場的西藏人也都陪我一起祈禱。他們的誠摯非常令人感動。政府當然也寫信來致哀,信是書名寫給負責發布訃聞的林仁波切,但是為了某種不明原因,卻直接交到我手上。接著發生了一件趣事。我讀完信,轉回去給他。他看完信,困惑的抓著頭皮來找我說:『照例說應該由我把信轉給你,現在卻顛倒過來。我該怎麽辦? 』這是我唯一碰到林仁波切說不出話的時候。 當然,母親過世我很難過,近年來,我見到她的機會因為工作與責任的壓力增加而變得愈來愈少。但我們精神上仍很親近,因此我有很大的失落感----每當隨員中的長者去世,我都有這種感覺。當然,時光流逝,上一代總會漸漸逝去,我四周比我年輕的人愈來愈多。事實上,我的政府人員平均年齡不到三十五歲。我覺得這有很多好處。今日西藏形勢帶來的挑戰,需要現代化的心靈才能應付。在舊日西藏環境中成長的人,不能了解那兒現在發生的轉變。面對這些問題的人,最好沒有記憶的包袱。此外,我們是為了下一代從事爭取西藏合法獨立的奮門,如果他們還願奮門下去,就必須由他們繼續。 一九八二年四月初,達蘭薩拉的三人談判小組飛往北京,討論西藏前途。領隊是當時噶廈資深成員竹謙圓滇南結,陪他前去的包括我的前任侍衛總管,一九五一年為嘎波嘎旺吉美擔任譯員的吞措塔希塔克拉,以及西藏人民大會主席羅提結稱結瑞。他們與中共高級官員晤面,雙方表明立場。 西藏人提出討論的各點,以我們祖國的史實為主。他們提醒中共,就歷史而言,西藏一直與中國分離,這項事實北京在強迫簽署十七點『協議』時,已完全承認。其次,我們的談判代表告訴中共:儘管我們一再吹噓誇大西藏的進步,但事實上。西藏人根本不滿意。他們建議中共根據這些事實,採取與事實相符的新方針。 一位談判者也問起,西藏人既然是外族,是否也應該擁有跟中共政府聲稱要給台灣的同族人相同或更多的權利。他得到的答覆是,台灣是因為尚未被『解放』,所以才提供它這樣的條件,而西藏卻早已踏上了輝煌的社會主義之路。 很不幸,結果顯示中共並沒有實質的事要談。他們教訓我們的代表,指責我們用考察團的資料歪曲真相。他們真正想談的只是要達賴喇嘛回去。為達到這個目的,他們提出有關我未來地位的五點清單。 一、達賴喇嘛應該相信中國已邁入長期政治穩定,經濟穩定成長及各族共和的新階段。 二、達賴喇嘛及其代表團應坦誠對待中央政府,不可拐彎抹角。也不應再以一九五九年的事件為遁辭。 三、中央政府誠意歡迎達賴喇嘛及其追隨者歸來。這是基於他們將對中國統一,加強漢藏及各族的團結及現代化計劃有所貢獻的期望。 四、達賴喇嘛的政治地位與生活狀況將與一九五九年以前相同。建議他不必住在西藏並擔任地方官職,但他當然可以經常回西藏。他的追隨者不必為工作與生活擔心,一切都將較過去改善。 五、達賴喇嘛若願回來,可向新聞界發布一分簡短聲明,其內容由他全權決定。 代表們回到達蘭薩拉後,中共政府發布了一份嚴重歪曲的會議記錄,指我們的觀點為『分裂主義』、『反動』、『中國人,尤其西藏人,都強烈反對』。中共對西藏的『新』政策開始顯得跟一九七○年代晚期的發展所指出者相去甚遠。正如一句西藏諺語所說的:『他們給你看的是黃糖,塞進你嘴裡的卻是白蠟。 』 談到中共提出與我有關的五點,我真不知道他們為什麽以為我會重視我個人的地位。整個奮門過程中,我關心的都不是我自己,而是我六百萬同胞的權利、幸福與自由。我這麽做不僅是為了爭界域,而是因為我相信,人類最要緊的就是本身的創造力。我更相信,為了實踐這種創造力,人必須自由。我放逐而擁有自由。作了卅一年難民,我已知道了它的一些價值。因此,在全體西藏人都能在自己的國家分享相同的自由之前, 我回西藏將是一項錯誤。 儘管跟中共政府從事的這些談判本身都毫無建設性,只要北京同意,我願意作一趟短暫的西藏之行。我希望跟我的同胞談話,親自了解真正的情況。對方反應良好,我們就準備於一九八四年派出一支先行部隊,為我次年到訪作預備工作。 同時,因為旅行的限制放寬,所以有相當多的西藏人開始來到印度。他們不斷前來,不過人數已漸漸減少。寫作本書時,已有將近一萬人來過印度,其中一半以上留下,大部分是希望在我們的學校與寺院大學就讀的年輕人。回去的人則大多出於不得已的原因。 我盡可能親自接見來自西藏的旅客。這些場合幾乎都令人非常激動:他們大都是悲傷而天真的人,衣衫襤褸,身無長物。我詢問他們的生活和家人的情形,他們答話時總是忍不住熱淚滾滾而下----在敘述親身遭遇時更是壓抑不住的號淘大哭。 這期間,我遇見曾赴西藏旅遊的觀光客人數也日益增加。有史以來第一次,外國人(主要是西方人)獲准進入這個雪國。不幸的是,中共官方從一開始就處處設限,開放政策實施之初,就只有加入遵守既定行程的團體才能入境,可以參觀的地方也少之又少。更有甚者,外人幾乎沒有機會跟西藏人接觸,因為大部分宿處都由漢人經營,這種地方僱傭的少數西藏人都只從事侍應或清潔打掃的粗工。 除了這些缺點,中共的導遊也只帶遊客參觀重建中,或重建完畢的寺廟,仍然是廢墟的所在從不在外人面前曝光。沒有錯,尤其在拉薩一帶,過去十年間有不少重建工作在進行,但我絕非處於私心才說這麽做只是為了取悅觀光團,事實上,不但住進這些重建寺廟的僧人都必須由中共官方審核,甚至他們還得犧牲修行的時間,親自動手搬磚挑瓦(資金由民間私人捐助),使人無法作出別種結論。 好在導遊都受過精心訓練,很少觀光客看穿這一點。如果他們問起,為什麽有這麽多重建工程,他們會被告知,很不幸文化大革命的破壞也蔓延到西藏,但中國人對四人幫的惡行造成的後果深表遺憾,他們震憾設法彌補過去可怕的錯誤。從來沒有人提起,大部分破壞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經成為事實了。 可惜的是,對大部分觀光客而言,西藏不過是個充滿異國風情的地方,是他們護照上的另一枚戳記而已。他們多看幾座寺廟,好奇心就得到滿足,廟中擠滿服飾多采多姿的進香客,更沖淡了他們的懷疑。但儘管大多數人受惑於表面假象,至少還有少部分人並非如此,這才是西藏開放觀光對我們真正的益處。這跟經濟或統計數字無關,只是一小群真正富於想像力與好奇心的遊客。他們會溜出兼負監視責任的導遊的視線,去看那些不希望被他們看到的東西,而且更重要的是,聽到那些他們不該聽的消息。 一九八一到一九八六年之間,西藏觀光客人數從一千五百人增加到三百萬人。從後來跟我們流亡政府接觸的人口中,我們得知中共所謂的『自由主義』,不過是空洞的口號。西藏人仍沒有言論自由,雖然他們私下明白的反對中共佔領我們的國家,卻從不敢公開談論。更有甚者,他們取得資訊的管道極為有限,舉行宗教儀式也要受管制。不需要太客觀就可以看出,西藏還是個警察國家,人民都在恐懼中忍氣吞聲。儘管毛澤東死後就有改革的承諾,他們仍然不曾脫離恐懼,現在他們更鬚麵對大批湧進的漢人移民,用壓倒性的人數威脅到他們的生存。 我遇見的很多觀光客都說,他們到西藏前,基本上都持支持中共的態度,但目睹的一切推翻了原來的觀念。同樣的,很多人說,雖然他們基本上對政治不感興趣,現在卻覺得必須改變立場。我記得有位來自挪威的男士告訴我,他最初很崇拜中共摧毀宗教的行徑,但當他第二度回到拉薩,看到了真相,他不由得問,他能幫助我的同胞什麽忙?我的回答正如我告訴所有提出相同問題的西藏出來的訪客一樣,就是把他目睹的事告訴越多的人越好。這樣,西藏的苦難才會有更多的人知道。 從新來者和觀光客口中不斷得到西藏的消息,因此一九八三年,中共與西藏發生新一波迫害浪潮時,我毫不感到意外。拉薩、日喀則、甘孜都有人被處決,昌都與開雷也有人陸續被捕,這次整肅涵蓋大陸全境,表面上,目標對準『犯罪與反社會分子』,但其實是為了對付異議分子。不過,儘管它似乎顯示中共官方的態度轉為強硬,這則消息也有其積極的方面,第一次,中共在西藏的活動透過派入西藏的國際通訊社特派員傳播到外界。 難民們擔心新的恐怖統治,是毛澤東時代強硬手段死灰复然的訊號,反應極為強烈。是保守派對鄧小平政權的反彈,或西藏再次陷入黑暗時代,都還言之過早。但很明顯的,我的先行部隊已無法成行,所以我的訪問也只好取消。 一九八五年五月中共對西藏政策已明顯的有重大轉變。胡耀邦提出中共駐西藏官員減少百分之八十五的要求未被採納,相對的卻展開鼓勵移民的大型宣傳活動。在『發展』的口號下,六萬名有技術及無技術的工人,在公家提供他們財務擔保、房屋補助及請返鄉假優待等條件的誘惑下,應召前往。同時,由於中共本身旅行限制放寬,很少人也以私人名義前往,希望找到更好的工作機會。就這樣,正如西藏人所說,來了一個中國人,後面至少跟十個,大批人潮湧至---持續至今也不減少。 同一年暮秋,甘地夫人遇刺身亡,西藏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朋友。我當時在倫敦赴德里途中,得知噩耗,深感震驚---不僅因為當天我正巧約定跟她及庫里辛那穆提(J. Krishnamurti)共進午餐而已。她的職位由她的兒子拉吉夫.甘地繼承,這位年輕的領袖一心為國,並樂意協助西藏的流亡社會。 拉吉夫·甘地秉性溫柔和順,心地極為善良。我還記得第一次見到他的情形。一九五六年我訪問印度時,應邀到他祖父尼赫魯府邸午餐。當時這位總理請我去參觀花園,我看見兩個小男孩在一座帳篷附近玩耍,他們想放一枚大沖天炮,卻放不上去。那正是拉吉夫和他的弟弟桑傑。最近,拉吉夫還跟我提起我要他們兩人守在帳篷裡的趣事。 不到一年的時間,羅桑桑天去世,西藏又失去一位重要的支持者。他年僅五十四歲,我在哀悼中也深感驚異。他參與第一支考察團的經驗,對他影響很大。他不能理解中共對西藏如此明顯的苦難不聞不問的態度。雖然他一向喜歡開玩笑取樂(他極具幽默感,而且有點粗俗),卻因而悶悶不樂很長一段時間。我相信若說他因心碎而死也不為過。 羅桑桑天的死令我非常難過,不僅因為我們一直情同手足,也因為他病危之際,我未能陪伴在側。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前往德里時,他當時正以西藏醫學研究所(Tibetan MedicaInstitute)主管的身分處理一些相關業務。他決定不跟妻子一塊爾回去。但到火車站,他又改變了心意。他的事還沒完全辦完,雖然有便車可搭,他還是決定留下。他就是這樣的人,永遠不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第二天他就莫名其妙的得了『感冒』,惡化成肺炎再加上並發黃疸病,三週後他就去世了。 今天我每想起羅桑桑天,最難忘的就是他的謙遜,他總是像一般西藏人那樣對為極為尊敬,而不是把我當作一個兄弟。比方說,每逢我回家或出門,他總是跟別人一起排在我住處的門口歡迎我,或祝我旅途順利。他不但謙遜,而且慈悲為懷。我記得有次跟他提到印度東部歐利薩(Orissa)的痲瘋病人聚居區。他跟我一樣,非常重視能幫助別人減輕痛苦的事。我說我希望西藏社區能夠對那些病患提供一些協助後,他就流著淚說,他個人願意盡一切努力。 我於一九七九年、一九八一年與一九八四年訪美,每次那兒的人都表示希望能為西藏人做些什麽。一九八五年七月,九十一位美國國會議員聯名寫信給當時的中共國家主席李先念,表示支持中共政府與我的代表舉行直接談判。信中鼓勵中共『盡可能考慮達賴喇嘛閣下及其人民極為合理而正當的願望』。 這是西藏第一次獲得正式政治支持---我認為這是我們目標的正當性終於開始贏得國際支持的一個令人鼓舞的跡象。進一步類似的證據,將使其他國家的人民也起而採取相同的立場。 一九八七年初,我接到前往華府美國國會人權高峰會議演講的邀請。我欣然接受,並定於該年秋季赴約。同時,我的很多老朋友都建議我趁這個機會,提出一些西藏要爭取的明確目標,俾便世界各地的正義之士認同。我認為這建議很好,於是開始組織我過去幾年中想到的一些觀念。 就在我動身赴美前夕,國會出版了一份有關人權被侵犯的新報告。其中指出,國會一九八五年致李先念的信遭受忽視:[沒有證據顯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曾對『達賴喇嘛合理而正常的願望』作任何考慮。]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在國會山莊演說,我提出的建議綱領自此被稱為五點和平計劃,它包括下列五點: 一、整個西藏劃為和平地區。 二、取消中共人口移民政策,因其已威脅到西藏民族的生存。 三、尊重西藏人民之基本人權及民主自由。 四、重建並保證西藏的自然環境,中共應中止在西藏生產核武器與棄置核能廢料。 五、對西藏的地位及中藏人民的關係立刻展開談判。 簡短的說明這些建議後,我請現場聽眾提問問題。這時,我注意到場中有些人看起來很像中國人,我問他們是不是,他們猶豫一會兒才回答是的,他們是新華社的人。此後,我發現每當我在海外公開演講,中共必然派人到場監聽。這些人通常對我都很友善,當他們偶爾否定我或諷刺我的時候,都會露出愧疚的表情。 我要大致說明一下五點和平計劃。第一點之中,我建議整個西藏,包括東部的西康與安多省份在內,都改為Ahimsa地區。 (Ahimsa 是個印度教名詞,意為和平與非暴力狀態)。這符合西藏作為一個愛好和平的佛教國家的地位,與中共已表示支持的尼泊爾以和平地區自居的宣言完全相同。如果能實現,西藏就可恢復其作為亞洲強權之間的緩衝國的歷史地位。 下列個點是 Ahimsa 地區的主要條件: 全西藏高原列為 非軍事區。 禁止在西藏高原生產、試驗、或存放核子武器及任何其他武器。 西藏高原將成為世界最大的自然公園,以嚴格的法律保護野生動植物;剝削自然資源的行為將審慎立法管制,以免破壞相關的生化系統;人類居住的地區將實施認可發展的政策。 禁止製造或使用核能,以及任何企圖會產生危險性廢料的科技。 國家資源與政策都將以推動和平與環境保護為目標。凡致力推廣和平及保護各種生命形式的組織,都會在西藏得到友善的接待。 推廣與保護人權的國際性與區域性組織,西藏都會加以鼓勵。 Ahimsa地區成立後,印度就可以從與西藏接壤的喜馬拉雅山區撤除軍隊與軍事設施---一俟簽訂足以滿足中共合法的安全需求,並且能建立藏、中、印及該地區其他民族之間互信的國際條約,就能實現。這對每個人都有利,尤其是中共和印度,不但能加强两國的安全,同時又能減輕維持大批軍隊駐守喜馬拉雅山未定界的經濟負擔。歷史上,中印從未起正面衝突。只有當中共部隊闖入西藏後,兩國才有疆界相接,在兩大強權之間造成緊張,促成一九六二年的戰爭。從此以後,危險的小紛爭就層出不窮。 歷史上一直是如此---中間設立一個廣大而友善的中立地區。改善中國人與西藏人的關係,首要之務是建立互信。過去三十年的浩劫中,幾乎有二十五萬西藏人死於飢餓、死刑、酷刑、自殺, 還有數万人被囚禁在罪犯營中,令人難以置信,現今唯有中共撤軍,真正的和解才能開始。西藏的大批佔領軍每天都在提醒西藏人他們所受的壓迫與痛苦。撤軍是未來與中共基於友誼與信任建立有意義關係的必要條件。 不幸的是,北京把我提議的這一部分,視為分裂的行動,其實這絕非我的本意。我的用意只是指出,為追求我們兩個民族之間真正的和諧共存,至少有一方必須作某種程度的讓步。由於西藏一直是受害者,我們西藏人已一無所有,沒有東西可以奉獻給中共,所以為了建立互信的氣氛,那些手持步槍的人應該撤走。這就是我所謂的和平地區:一個沒有人攜帶武器的地區。這不僅有助於建立信任,對中共的經濟也會有很大的幫助,他們可以節省在西藏駐軍的大筆開銷,對一個開發中國家而言,這筆開銷可以說是龐大的浪費。 我的五點和平計劃第二點,與西藏作為一個獨立的民族所面臨的生存威脅有關,也就是中國人人口流入西藏的問題。一九八○ 年代中期,中共的漢化政策已極為明顯:有些人暗地裡稱之為『最後的解決方案』。他們籍此使土生土長的西藏人減少到微不足道的比例,變成自己祖國里的少數民族。這一定要中止。漢人平民大規模移入西藏,直接違反了第四次日內瓦大會的決議,現在我國東部,漢人人口已超出藏人甚多。以我的出生地,現在被劃歸青海省的安多為例,據中共統計資料,當地有二百五十萬漢人,僅七十五萬藏人。即使在所謂的西藏自治區(亦即西藏中部與西部),我們的資料顯示,漢人也已多於藏人。 這套移民政策並不新鮮。中國曾有系統的在其他地區運用。不久之前,發源於中國東北地方的滿族還是擁有自己的文化與傳統的獨立民族。今天的東北地方只剩二到三百萬的滿族人,漢人卻多達七千五百萬。又如今天中國人稱為新疆的東土庫斯坦,漢人已由一九四九年的二十萬人增為今天的七百萬人,佔全部當地人口一半以上。中國殖民內蒙古後,漢人增為八百五十萬,蒙古人僅二百五十萬。我們估計,目前全西藏有七百五十萬漢人,多於藏人的六百萬。 西藏民族要繼續生存,漢人移民必須立刻停止,漢人屯墾民必須獲准回內地,否則,西藏人將淪為吸引觀光客的噱頭和光榮歷史的遺跡。目前漢人之所以留下似乎主要由於經濟誘因;此地情況並不適合他們,漢人罹患高山病的比比皆是。 我建議的第三點與西藏的人權有關。這一定要尊重。西藏人應有在經濟、文化、知識、靈性等方面發展的自由,並享有基本的民主自由。西藏侵犯人權的情形全世界最為嚴重,國際特赦組織及其他類似機構都可以證明。西藏的歧視行為在中共所謂的『隔離與同化』下,與種族隔離政策無異。西藏人在自己的國家淪為二等公民,被剝奪所有基本民主權利與自由,由佔領的殖民政府控制,所有實權都掌握在中共官員、共黨及人民解放軍手中。雖然中共准許藏人重建佛寺,朝拜進香,卻嚴禁一切與宗教有關的學問授受。因此,雖然流亡在外的西藏人,根據我一九六三年草擬的憲法,擁有民主權利,但我成千上萬的同胞仍然因他們對自由的信念,在監獄或勞動營中受苦。在西藏,效忠中共的西藏人被稱為『進步』,效忠自己國家的西藏人卻被打成『罪犯』,鋃鐺入獄。 我的第四項建議,呼籲為重建西藏的自然環境而努力。西藏不應用於生產核子武器或堆置核能廢料。西藏人一向尊重各種生命的形式。這這與生俱來的感情,因佛教信仰嚴禁殺生而更為加強。中共入侵之前,西藏是一片清新、美麗,未經破壞的野生環境庇護所,擁有其獨特的自然環境。 遺憾的是,過去數十年來,西藏的野生動物幾乎完全被摧毀,很多地區的林木已無法恢復原狀。整個西藏脆弱的環境力受損極大---尤其因為這個國家的高海拔與乾燥,植物生長需花比低海拔潮濕地區更久的時間。因此,僅餘的一切更須加以保護,並努力扭轉中共對西藏環境不公平的肆意破壞造成的惡果。 因此當務之急是中止生產核子武器,更重要的是防範棄置核能廢料。目前中共不但打算在此處理它自己的廢料,也計劃進口外國廢料牟利。此舉的危機顯而易見,不但危害現在生存於此的人,他們的後代也將同受其禍。更有甚者,本地無可避免的問題輕易便會轉變為全球性的災難。把廢料交給中共,因為把這些東西丟在地廣人稀,科技相當落伍的區域,只是解決問題的權宜之計。 我在要求就西藏未來的地位舉行談判的呼籲中,表達了我以坦誠修好的態度解決問題的意願,希望找出一個對所有的人----西藏人、中國人,以及地球上每一個人---都有長程利益的方案。我的動機是經由地區性的和平促進全世界的和平。我決不以批評中共為能事,相反的,我願意盡一切可能來協助中國人。我希望我的建議對他們有益。不幸的是他們全部視之為分離主義(其實,我在談及西藏的未來時,從未提起主權問題),北京立刻用強烈的措辭駁斥我的演說。 這並不令我感動意外。西藏人的反應雖出乎我的預料,卻也沒有令我太驚訝。我在華府演說後沒幾天,就傳來拉薩舉行大規模示威的報導。 |
| © The Office of His Holiness the 14th Dalai Lama. e-mail: service@dalailamaworld.co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