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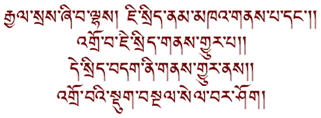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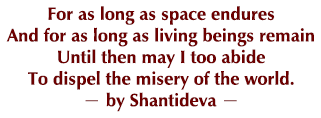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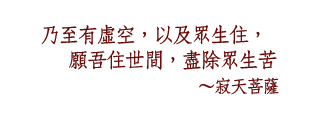 達賴喇嘛格言
愛心與慈悲是不會浪費的,它們總會另有一番氣象。讓受者幸福,同時也讓施者幸福。
相關連結
|
藏曆:2152 木蛇年
⌘ 流亡中的自在 ⌘
第十章:披著僧袍的狼
澤仁多瑪也在一九六四年去世,她的工作由我的妹妹傑春佩瑪接辦,她的勇氣與決心毫不遜色。今天,達蘭薩拉西藏兒童村中的育幼院仍經營得有聲有色。
西藏兒童村在各屯墾區都設有分支機構,目前共收容教養六千多名兒童,達蘭薩拉的兒童總數則在一千五百人左右。開始的時候大部分資金由印度政府提供,目前大部分開銷則改由慈善組織『國際緊急救難組織』(SOS lnternational)負擔。三十年來,目睹我們在教育方面的努力開花結果,令人十分欣慰。現在已有兩千多個孩子大學畢業---他們大多就讀印度大學,但到西方求學的人日漸增多。我向來極注重教育計劃,尼赫魯說過,孩子是我們最珍貴的資源,我一直牢記在心。 早期的學校只是一些破舊的建築物,印度老師在此教一些背景極為懸殊的兒童。現在我們已擁有健全而夠水準的西藏教職員,但也仍有很多位印度教育工作者參與。我要向這些人和他們的先驅者致最大的謝意,對那些為我的同胞奉獻大部分人生,不辭環境艱苦與路程偏遠的人,我實在無法充分表達感激之忱。 令人失望的方面則是,很多孩子(尤其是女孩)未能完成教育。這有時是因為他們自己缺乏興趣,但有時則是家長的短視。我只要一有適當機會,就會說服家長,他們有責任不利用孩子謀眼前的近利,否則只受到部分教育的孩子,會因教育水準不夠而坐失人生良機。這樣會造成他們對人生失望與貪婪的心理。 夏士崔(Lal Bahadur Shastri)繼尼赫魯為印度總理。儘管他只當權三年,我卻經常見到他,而且非常敬重他。夏士崔如同尼赫魯一樣,善待西藏難民,甚至也是位政治上的盟友。 一九六五年秋天,泰國、菲律賓、馬爾他、愛爾蘭、尼加拉瓜與薩爾瓦多在聯合國提出一項決議草案,重新討論西藏問題。印度在夏士崔堅持下,也投票支持西藏。他當政期間,情勢似乎很可能使西藏流亡政府獲得印度承認。不幸的是這位總理活得不夠久,而印度又再次參戰,這次的對手是巴基斯坦。戰爭於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爆發。 達拉薩拉距印巴邊界不到一百英里,我得以親眼目睹戰爭的悲慘後果。戰役開始不久,我就離家前往一個我常去的南部屯墾區。當時已是夜晚,因實施燈火管制,我們開往巴丹庫特車站三小時路程中,都不能開車燈。一路遇到的其他車輛都是軍車。我記得當時我心想著,老百姓都被迫躲起來,由國防武力出動,實在是很可悲的狀況。但事實上,這些人都跟我一樣,只不過是凡人。 好不容易到了火車站,我聽見密集轟炸巴丹庫特機場的砲聲。一度還有噴射機從頭頂尖嘯而過,過一會兒就見高射砲曳光彈射入半空。這些可怕的聲音令我膽戰心驚,不過好在害怕的不止我一個。我搭火車出站的速度從沒有像那晚那麽快過。抵達南方,我先去看拜拉庫普的原始難民屯墾區,當時是九月十日,它已成為三千兩百人的家,還有磚瓦建築的永久性住宅,鑽井砍樹的工作也都已完成,大家熱忱的照原定計劃展開農耕,每個人名譽上擁有一英畝土地,不過實際上是採合作耕種制度,只保留一部分供私人種自家食用的應時蔬果。主要的作物是稻米、玉米及粟 米。我很高興看到這樣的進步,也更加強了我認定積極展望與決心,能發揮無比力量的信念。 整體而言,情況大有改善。我不必再面對瀕臨絕望邊緣的人,也不必再作一些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承諾。但儘管屯墾者的堅忍不拔已得到了回報,他們的生活還是相當困苦。 最初跟印度政府擬訂屯墾計劃時,我們是希望屯民五年之內就能自給自足,有多餘的農產品可資出售,開始對印度的經濟有所貢獻。但我們沒有料到這些人未經訓練,大部分都缺乏農耕知識。無分商人、僧侶、軍人、游牧者及單純的村民,都一頭栽進這項他們一無所知的新行業,其實我們不該那麽樂觀。 印度的熱帶農業跟高緯度的西藏農業相去甚遠,所以即使對農耕略有所知的人,也得從頭學習用牛耕田及維修耕耘機等。因此,即使經過將近五年,營區的狀況仍相當落伍。 但現在回顧起來,我覺得一九六○年代中期還是該算西藏屯墾計劃的一個高潮:大部分整地工作都已完成,在國際紅十字會及其他人士的協助下,大部分難民都享有基本的醫療照顧---農耕機械也都很新,不像現在那麽陳舊,亟待更換。 一九六五年這一次,我在拜拉庫普停留一周到十天左右,接著我沿路拜訪了米索(Mysore)、烏塔馬康德(Ootamacund)及馬德拉斯(Madras),最後來到印度最有文化氣息的省份喀羅拉(Kerala)的省會崔凡舉姆(Trivandrum)。我應邀住在省長家,但最後由於北方的戰爭,我只好在這兒住了數週之久。戰爭危險一直在升高,達蘭薩拉已落了兩枚炸彈。不過,這段時間並沒有浪費。 我住在省長拉吉巴凡(Rajbavan)公館的房間,正好在廚房對門,一天我偶然看見他們殺雞做午餐;目睹雞的脖子被扭斷,我不禁想到,這可憐的動物不知受了多少苦。這一覺悟使我滿心悔恨,我決定從此開始吃素。我前面已提過,西藏人不一定吃素,因為西藏蔬菜很稀少,肉類反而是我們的主食,但有些大乘經典規定,出家人都應該戒葷腥。 為了確定我所下的決定,我請他們送來食物。我仔細觀察以英國口味烹調的雞,加了洋蔥與醬汁,聞起來十分誘人。但我覺得拒吃一點也沒有困難。從那時開始,我就完全遵奉茹素的戒律,而且也不吃魚和蛋了。 我很能適應新的戒律,而且覺得非常滿足;嚴守紀律帶給我一種成就感。早在一九五四年,我在北京就曾經在宴會上跟周恩來及另一名政客談過這問題。另外那個人自稱吃素,但他卻吃蛋。我指出因為雞從蛋來,蛋絕不能視作素食。我們發生強烈的爭執---直到周恩來用外交手腕打斷我們為止。 印巴戰爭於一九六六年一月十日結束。但一件不幸的事沖淡了歡樂的氣氛----夏士崔總理在塔什幹與巴基斯坦總統阿育布罕(Ayub Khan)談判和約時去世。和約簽訂後數小時內,他就與世長辭。 夏士崔雖然身材矮小贏弱,是個相當不起眼的人,卻擁有過人的心智。脆弱的外表下是位傑出的領袖。他不像很多其他位居要津的人,他是個勇敢而有擔當的人,絕不讓事件牽著鼻子走,而會盡力掌握它們的發展方向。 不久,我應邀參加他的火葬禮。這真是件令人難過的事,尤其是因為這是畢生第一次從近距離看一具死屍。我雖身為佛教徒。每天觀修死亡,卻沒有這方面的經驗。我記得看著他僵硬的身軀安放在火葬架上,回憶起他的言行舉止,以及他跟我分享的一些私人見聞。他曾告訴我,他是個嚴格的素食者,兒時他曾追一隻受傷的豬兒繞圈子跑,直到力竭而死。這樣的結局令他惶恐萬分,所以他立誓再也不吃任何有生命的動物。如今不但印度失去了一位一流的政治家,全世界失去了一位開明的領袖,人類也失去了一位真正慈悲的仁者。 向夏士崔故總理致最後敬禮後,我回到達蘭薩拉的途中,走訪了德里若干收容作戰受傷者的醫院。我見到的大多數是軍官,走在病床間,聽見家屬的哭聲,我告訴自己,戰爭只有一個結果:帶給人類無比的痛苦。衝突產生的其他結果,事實上都可以用和平的手段達成。唯一差堪安慰的是,這些醫院中的傷患都得到良好的照顧:很多其他參戰的人不見得能享用這麽好的設備。 兩週後,英德拉甘地夫人宣誓就任總理。因為我每次見她的父親,幾乎也都會見到她,我覺得她很親切,我有理由相信她對我也有同感。她不止一次推心置腹的把令她心煩的人或事向我傾吐。因為我自己覺得夠了解她,所以在她第一個任期將屆時,我提醒她,領袖必須跟老百姓保持聯繫。 我自己從小就學到,希望當領袖的人一定得時時親近老百姓,否則很容易被周圍的顧問與官員誤導,他們很可能處於私心,不希望你把事情看得太清楚。 我同樣感謝英德拉比照印度歷任總理,同樣照顧西藏難民。她是西藏家園基金會(Tibetan Home Foundation)(基地在莫梭瑞)的創始會員,在教育方面尤其盡心。她重視教育的程度,如同她的父親卓具遠見。雖然印度狀態緊急,有人對她不滿,甚至還有人稱她為獨裁者,但我認為,一九七七年三月,她面對選舉結果,交出政權,表現極有風度。在我看來,這是絕佳的民主範例;雖然國會內外都存在著許多衝突,當她必須退出的時候,她做得非常乾脆。我對美國的尼克森總統也持相同的看法。往往領袖權轉移都會發生流血事件。只有真正文明的國度裡,國會的程序才能超乎個人私利之上。 同一時期,中共的內政發展就截然不同。從一九六○年代中期,直到毛澤東一九七六年去世為止,全中國都陷入一片腥風血雨的混亂之中。文化大革命的真相很多年後才呈現在世人眼前,在這場漫無目標的混亂裡,大權旁落到以女皇帝自居的江青手中。我也才算看清了共黨領導人在一心一德的假面具下,私底下門得你死我活的真相。 不過,當時究竟混亂到什麽程度,我們只能臆想而已。我跟很多西藏人一樣,知道我們心愛的故國發生了可怕的事,但音訊全然不通;唯一的消息來源是偶爾獲准越過邊界的尼泊爾客商,他們不但所知少,而且往往早已過時。例如,直到事發一年後,我才知道一九六九年西藏好幾個地區發生大規模抗暴。據某些報導指出,在中共報復行動中被殺的人數比一九五九年那次更多。 我們現在知道,這種騷動發生過很多次。當然,這時我已經跟北京那些稱我為『披著僧袍的狼』的領袖沒有直接聯絡。我成為中共仇視的焦點,在拉薩也常被詆毀為一個裝成宗教領袖模樣的騙子。中共說我是個賊、兇手兼強暴犯,他們還暗示說我跟甘地夫人私下發生多次驚世駭俗的穢行。 就這樣,西藏難民陷入歷時十五年的黑暗時期,回家的希望比我們剛開始流亡時更黯淡。但黑夜當然也是個修養的機會,這期間我們的屯墾計劃總算有了成果。愈來愈多的人加入全印各地的新屯墾區,不再四處漂泊。同時,也有一部分難民離開印度,在全世界其他地區建立小社區。目前,我們約有一千二百人在英國,其他歐洲國家約各有數十人,還有個年輕人組的家庭住在愛爾蘭。 隨著第二波移民屯墾計劃展開,西藏流亡政府也設立了幾個海外辦事處,分別位於加德滿都、紐約、蘇黎世、東京、倫敦及華盛頓。西藏駐外辦事處除了照顧當地藏人的福利,也盡可能傳播有關我們的國家、文化、歷史,以及流亡所在地和故鄉生活的資訊。 一九六八年,我打算離開住了八年的史瓦格阿夏蘭姆(Swarg Ashram),搬入一棟名叫布林小屋(Bryn Cottage)的小房子。這座建築房子雖沒有比較大,但它的好處是周圍有新建的一批房舍,足以容納我的內務辦公室和印度安全室,還有間會議室和我私人的辦公室。西藏流亡政府現在已成為有數百名人員的組織,他們大部分遷至不遠的辦公區。在進行重新調配的同時,我母親也在不大情願的情況下,遷入新居喀什米爾小屋(Kashmir Cottage),使我得以恢復出家人的生活。 不久後,我著手重建南嘉寺院,該院的僧人原本住在史瓦格席蘭姆上方的一所小屋裡,現在則遷至距我住所不遠的另一棟建築。一九七○年,一間名為春拉康(Tsuglakhang)的新寺院也完工,自此我才有適當的場地,根據西藏傳統曆法,舉行各種儀式。今天南嘉寺旁並成立了一所佛教辯論學院(School of Buddhist Dialectics),保存僧院中論辯的藝術。下午時分,寺外廣場上經常濟滿了身著栗色僧袍的年輕僧人,為考試作練習,不時拍手或搖頭。 一九六三年,我召集各教派領袖以及苯教代表開會。我們討論各種困難以及克服之道,如何保存並傳播西藏佛教文化的各種策略。經過數日討論,我們獲得充分的信心:只要有適當的設施,我們的宗教一定能生存下去。我在重建寺院後不久,又在南方的卡納塔卡(Karnataka)省重建了甘丹、哲蚌(Drepung)與色拉(Sera)寺,最初是把布哈杜爾劫後餘生的一千三百名僧人安置其中。 現在我們流亡已邁入四十年關卡之際,欣欣向榮的寺院人口已超過六千人。我甚至敢說:我們的和尚人數已經太多了;畢竟重要的是這些人潛心向佛的誠意,而不在人多勢眾。 一九六○年代末期展開的另一項文化事業是西藏文獻圖書館,館中不僅搜羅四萬多種藏文原始經典,也出版英文及藏文書籍。一九九○年,它出版了第兩百種英文著作。圖書館外觀為傳統西藏風格,除了藏書之外,它還有一個博物館,收藏多件由難民帶到印度的文物。他們能隨身攜帶的物品有限,很多人選了唐卡、經書或其他宗教手工藝品。通常他們都把這些東西奉獻給達賴喇嘛,我又轉贈給各文化機構。正式遷入布林小屋前,我大病一場,數週才痊癒。一九六六年初,印巴衝突告一段落,我回到達蘭薩拉,熱心開始吃素。西藏蔬菜很少有不加肉的,而廚子也經過相當一段時間才學會如何不用肉而使菜一樣美味適口。同時,印度朋友告訴我,多喝牛奶及吃各種核仁來補充營養的重要性。我恪遵他們的勸告---不料二十個月後卻羅患了嚴重的黃疸病。 第二天,我吐得很厲害。此後兩三個星期,我完全沒有食慾,而且感覺極度疲倦,動一動就得使出全身的力氣。更明顯的是,我的皮膚變成薑黃色,看起來倒頗像佛陀!過去有人說,達賴喇嘛像黃金籠裡的囚徒,這一回我連身體都變成金色了。這場經診斷為B型肝炎的病終於痊癒了,但我消耗了大量的西藏藥品(下一章我會作詳細介紹)。我再次對吃感興趣,醫生叫我少吃油膩,減少核仁與牛奶的攝食量,同時我必須恢復吃肉。他們擔心這場病會對我的肝臟造成永久性的傷害,因而縮短我的壽命。我請教的多數印度醫生都持相同的看法,因此我只好心不甘情願的放棄吃素。今天我除了靈性修養上的特殊需要,日常都吃肉。很多模仿我的榜樣卻遭到相同下場的西藏人,也都是如此。 我住在新家從一周開始就很愉快。這房子跟史瓦格阿夏蘭姆一樣,最初由英國人所建位於一座小山頂上,有一個小花園,四周有樹。它眺望達拉達山與下面的達蘭薩拉山谷,視野絕佳。除了門外有片廣場可以供千人聚會演講外,它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花園。我立刻開始工作,栽植了多種不同的果樹與花卉,一切都親自動手,因為園藝是我的一大愛好。可惜大部分樹長得都不好,果子也不甜,不過很多動物,尤其是小裊經常來此,帶給我不少安慰。 我喜歡觀察野生動物尤勝於園藝。為此我特地在窗外搭了一個鳥食架,它周圍有鐵絲和網,以防較大的鳥和猛禽闖入,把小鳥嚇跑。但有時這種措施還不夠,我只好不時取出我抵達印度後才賣的空氣槍,準備給這些貪婪的小傢伙一個教訓。兒時我在諾布林卡宮花了不少時間練習使用第十三世達賴喇嘛留下的老式空氣槍,所以我的槍法很準。當然我不會殺死它們。我只想使們覺得痛,得到一個教訓。 布林小屋的日子跟過去一樣忙碌。每年冬季我都到屯墾區巡視,偶爾我也講經。我繼續研究宗教,此外我也開始學習西方思想,尤其是在科學、天文與哲學等方面。空間時間我重溫一向喜愛的攝影。在我十三四歲的時候,我的稱夏、跛足的色空仁波切送我一架箱型相機,那是我的第一架照相機。 最初,我把拍好的底片交給他拿去沖洗。他總假裝相片是他照的(以免我萬一照了什麽不宜達賴喇嘛拍攝的鏡頭而感到尷尬),送到一名商人那兒。照片得運到印度沖洗。這程序總是令他非常緊張,因為如果照出來的東西不成體統,他必須負責!不過後來我在諾布林卡建了一個暗房,而且從我一位官員吉美搭仁那兒學會沖洗照片的技術。 我搬入新家庭後重拾的另一個老嗜好是修理手錶。現在空間比以前寬敞,我可以撥出一個房間充作工作室。就我記憶所及,我一直對鍾錶和念珠著迷,這一點我跟十三世達賴喇嘛很像。往往我比較我們之間個性上的差異,就覺得我不可能是他的轉世,但念及我們對鍾錶和念珠的相同愛好,我就恍悟這樣的安排沒有錯。 我很小的時候,雖然隨身帶著我的前身的懷錶,但我真正想要的卻是一隻手錶---不過有人勸我不要戴。我一長大到足以說服色空仁波切我確實需要手錶時,我就要他從拉薩市上賣了一隻勞力士和一隻奧米茄給我。說來似乎難以置信,早在中共闖入大軍來教化我們之前,拉薩已賣得到瑞士名錶。事實上,市場上幾乎沒有賣不到的東西,從英國香皂到上個月的生活書刊,都很容易到手。 不消說,新錶一拿到手就被我拆開。我第一次看到機械結構的各個微小零件,不由得懊悔自己太過輕率。但不久我就學會如何把它們都裝回去,及如何調整手錶走快走慢。所以今天終於能有間工作室可以做這些事,真是令我非常愉快。我替家人和朋友修好很多只看來已無藥可救的錶;到今天我還把各種工具留在手邊,但我已不大有時間再從事這方面的工作了。更何況現在做的錶,很多在打開時都難免會擦傷;我恐怕我交換給人家的錶雖然能運作正常,但外表卻不及原來的美觀,不免使他們感到失望了。 大致上,我多多少少設法趕上現代科技,但是電子錶當然超出我的能力範圍。我只有一兩次失敗,一次是一隻極漂亮的派提,菲利普錶,是羅斯福總統送我的禮物,有秒針和日期。不但我修不好,送去請專業修錶匠修理,他們也是一樣無能為力。直到幾年前,我趁訪問瑞士之便,把它帶到原製造商那兒修理,才恢復運轉。好在我逃離拉薩時,它是在一名印度修錶匠手中。還有一隻修不好的錶屬於我政府裡的一位官員:我很遺憾的承認,我把錶裝在信封里送回去---拆成一片片零件。 我也要趁此談談我在印度養的三隻貓。第一隻於一九六○年代末來到我家。是一頭黑白斑點的雌貓,名叫哲仁。有很多優點。最主要的是友善。我對家中寵物除了一進我家們就非成為和尚或尼師不可之外,其他的約束不多,但哲仁有個教我這個佛教徒難以容忍的缺點----見老鼠就非追不可。我不得經常管教。很不幸的,就因此送了命。我有次逮到在我屋子裡殺死一隻老鼠。我朝大吼,急忙爬到布幔上,一不小心失足跌了下來,受到重傷。雖然我盡可能悉心照顧,幾天後還是死了。 不久之後,我在花園裡撿到一隻小貓。顯然已遭母親遺棄。我抱起,發現跛了一隻後腿,跟哲仁死時一模一樣,我把這隻小貓帶回家照顧,直到能重新行走為止。也是雌貓,但長得比較漂亮,性格也比哲仁溫順。跟兩頭狗也處得很好,尤其喜歡躺在桑吉毛茸茸的胸前。 在這隻貓繼兩隻狗死去以後,我決定不再養寵物。正如我的親教師,熱愛小動物的林仁波切所說的:『寵物到頭來只成為主人另一個焦慮之源。 』更何況,從佛教徒的觀點看來,當眾生需要你掛念禱告時,只照顧一兩頭動物是不夠的。 不過,一九八八年冬季,我正好注意到面對我前門的廚房裡,有隻生病的小貓跟著母貓。我驚訝的發現也跛了腳,就跟前兩隻貓一樣。因此我用吸管餵----西藏草藥和牛奶,直到能自立生活為止,現在已成為我家的一員,本書寫作的時候,還沒有名字:早晚會有的。非常活潑而好奇,家中每次有客來訪,一定會來查看。到目前為止,都很守規矩,不追逐別的動物,但有機會的話,卻會偷吃我桌上的食物。 我觀察動物有一個心得----即使經過訓養,它還是會不顧生活的舒適,一有機會就跑到外面去。這促使我更加相信自由是所有生物的基本需求。 對我而言,三十一年流亡生涯最重要的一項收穫,就是有機會跟各行各業的人晤面。好在印度是一個自由國家,我要見誰都不受限制。 我偶爾會遇見一些真正傑出的人物,有時也會碰到一些令人討厭,甚至心理有問題的人,但一般而言還是普通人居多。 我見到人總以盡量幫助他們和向他們學習為目的。 有時人們在我面前表現得很笨拙,但就我記憶所及,我跟所有的訪客分別時都成了朋友。我相信這都是以誠待人的結果。 我尤其喜歡跟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包括來自不同的宗教傳統)見面。庫里辛那穆提(J. Krishnamurti)是個著名的例子。他給我很深的印象,他思路敏捷,學問淵博,雖然外表溫和,他對人生及其意義的看法卻十分明確。我也見到很多從他受教,獲益非淺的人。 這期間我最快樂的回憶是有幸接待美國本篤教會的湯瑪士.墨頓神父。他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來到達蘭薩拉,數週後他就在泰國去世。我們連續三天見面。每次共處兩小時。墨頓身材中等,體格健碩,頭髮比我還少,但並不是因為像我一樣剃度才如此。他穿一隻大皮鞋,厚重的白色法衣上還繫著一條粗大的皮腰帶。但比他令人難忘的外表更予人深刻印象的是他煥發於外的內心生活。我看得出他是個謙遜而極具靈性修養的人。這是我第一次跟基督教人士相處而受到如此精神上的感動。後來我也遇到其他有類似修養的人,但透過墨頓,我才知道『基督徒』一辭的真正意義是什麽。 我們的會晤氣氛非常愉快。墨頓極具幽默感,且見多識廣。我稱他為天主教「格西(geshe)」。我們談論雙方都感興趣的知性與靈性方面的問題,並交換有關院修行的資訊。我對西方的僧院傳統甚為好奇,他告訴我很多令我意外的事,例如基督教沈思時不需要擺出特別的姿勢,而據我所學,姿勢與呼吸的方法都非常重要。我們也討論到基督教僧侶與修女的誓辭。 墨頓則希望多了解菩薩的理想。他還希望找位能為他啟蒙密教的上師。整個而言,我們的交談甚有裨益----尤其我從而發現佛教跟基督教有很多相似之處。因此我聽到他忽然死亡的消息,極感難過。墨頓可視為我們兩種迥然不同的宗教文化之間的一座有力的橋樑。最重要的,他幫助我了解,所有教人相愛與慈悲的主要宗教,都能產生善良的人。 自從與墨頓神父晤面後,我跟其他基督徒也有多次接觸。我訪問歐洲時,曾參觀很多不同國家的修道院,每次都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所見僧侶對他們的神召表現的虔誠,令我羨慕。雖然他們人數不多,我卻感覺得出,他們有極高的信仰誠意。相對的,我們西藏人即使在流亡之中,也維持相當大的僧侶人口---佔據流亡人口百分之四到五----但虔誠的程度卻不見得都那麽高。 我也很佩服基督教各教派透過慈善機構,在健康與教育方面所做的實際工作。印度就有很多了不起的例子。我們在這方面有很多該向基督教的弟兄姊妹學習之處:如果佛教徒也能對社會作類似貢獻,一定很有用。我覺得佛教僧侶往往只是嘴里大談慈悲,做得卻很少。我曾數度與西藏人及其他佛教徒談及此事,積極鼓勵建立類似的機構。但我同樣覺得,我們也有值得基督徒學習之處。比方說,我們沈思打坐與把思考集中於一點的技巧,或許能在宗教生活的其他方面對他們有所幫助。 一九六○年結束時,我安排十萬名西藏流亡人士在印度、尼泊爾及不丹屯墾的夢想,也達初步完成的階段,因此雖然來自西藏的少數消息都令人沮喪,我仍然以實際而有根據的樂觀態度展望未來。不過,兩組非我控制之內的事件提醒我,目前的處境依舊危機重重。 第一組事件與四千名左右定居在不丹的難民有關。不丹王國位於印度東方,西藏中部烏昌省南方,地處偏遠。它像西藏一樣,地形多山,人民信奉與我們同一派的佛教,極為虔誠。但跟西藏不同處在於它是聯合國的正式會員。 不丹已故的國王對流亡到他國內的西藏人非常仁慈。在印度政府協助下,他為我的同胞提供土地和交通,並協助建立農業屯墾區。 開始時一切順利,西藏人都很滿意。一九七四年我在菩提伽耶舉辦第一次時輪金剛灌頂法會時,見到他們一群人,得知他們都生活得很好,我也很高興。他們對地主讚譽備至,尤其是最近登基的新王吉美旺秋。他處理國事的成熟穩重,令所有的人佩服。但是不過幾個月,突然有了變故。西藏社區二十二位受到敬重的人士突遭逮捕,受酷刑拷問後,未經審判就關入首都聽普的監獄。我的私人代表拉汀(與先王有親戚關係)也在其中。這消息令我很難過,我覺得應先進行徹底的調查(雖然我根本不相信這些人所受陰謀叛亂的指控)。但從未有調查,真相始終不明。最後我才知道,這些西藏人原來被利用作不丹政府內部糾紛的替罪羔羊。 這次不幸事件後,很多西藏人決心離開不丹。但留下的人此後的生活也很平靜,儘管有些不利於他們的懷疑與敵意仍然存在。無論如何,我還是很感激不丹的人民與政府為我的同胞所作的一切,並確信我們傳統的友誼未來一定會恢復。 另一不幸的事件與美國中情局訓練、供給裝備的游擊隊有關,他們繼續用暴力手段為爭取西藏自由而奮門。我不止一次從嘉洛通篤及其他人口中,聽到這類行動的情形,但從未與聞整個的細節。不過我知道,一九六○年,尼泊爾北部最偏遠,與西藏交界的木斯塘(Mustang)地區,成立了一個游擊基地。由數千名流亡人士的壯丁組成的部隊駐紮在那兒(但只有少部分人實際受過美國人的訓練)。不幸這個基地的後勤補給未經妥善規劃,以至多次狙擊行動都遇到困難。但不管怎麽說,比起在西藏內部從事門爭的那些勇敢逾常的自由門士面臨的危險,當然又不算什麽了。這處基地開始運作後,游擊隊曾多次痛擊中共部隊,有次還摧毀一個運輸隊。這次突擊擄獲一批文件,載明一九五九年三月到一九六○年九月之間中共在拉薩屠殺八萬七千人。這些勝利頗能鼓舞士氣。但缺少持續有力的後續行動這項事實,恐怕只是帶給西藏人民更大的痛苦。更糟的是,這些活動予中共政府把西藏爭獨立運動指為外國陰謀的口實----但獨立運動當然是全西藏主動的。 美國自從一九七○年代承認中共,就斷絕了對西藏的支持---這證明他們的援助只是反共政策的一環,而不是真心要恢復西藏的獨立。 不過游擊隊決心繼續戰門下去,這使得深受其擾的中共要求尼泊爾政府解除木斯塘部隊的武裝,儘管這些西藏人跟尼泊爾政府之間暗中必定有某種協議,是不問可知的事實。但當尼泊爾試圖這麽做的時候,游擊隊悍然拒絕,他們說,即使此後要跟尼泊爾軍隊作戰也要打下去。 我雖然佩服游擊隊的決心,卻從不支持他們的活動,這時我知道我必須干預。我知道唯有親自提出請求才能打動他們。因此我指示前任侍衛總管塔克拉(PTTakla)帶我的錄音信去見他們的首領,我在信中指出,跟尼泊爾作戰沒有意義,尤其因為有數千名西藏難民在尼泊爾定居,戰爭勢必連累他們,何況他們本該感謝尼泊爾政府。因此他們該放下武器,開始和平的定居下來。西藏的奮門絕非一蹴可幾,必須從長計議。 後來,塔克拉告訴我,很多人有被背叛的感覺----少數幾位領袖竟刎勁自殺也不肯離開。我聽到這消息真是萬分旁徨。我對呼籲自由門士撤退一事的感覺無可諱言是相當複雜。要求他們違反對西藏無與倫比的勇氣、忠誠與愛,似乎是個錯誤,但我從內心深處知道,只有這麽做才正確。 絕大部分游擊隊放下了武器,但少數人(大約不到一百人)無視於我的請求,結果被尼泊爾軍隊逐出國界。最後他們遇到埋伏,壯烈戰死。這可能正符合他們的心願,而西藏流亡史上最悲慘的一頁也於焉結束。 |
| © The Office of His Holiness the 14th Dalai Lama. e-mail: service@dalailamaworld.co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