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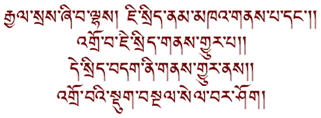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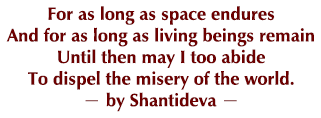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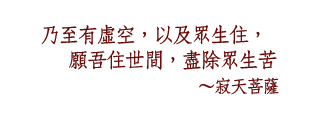 達賴喇嘛格言
我深信阻礙我們深切體認彼此間相互依存關係的一項主要因素,是我們太過強調物質發展。我們太著迷於追逐它,不知不覺地,就忽略了慈悲、關懷與合作等最重要的基本性質。如果我們不了解某人,或不覺得跟某人或某團體有瓜葛,我們便易於忽視他們的需求。然而,人類社會的發展卻需要大家相互幫助。
相關連結
|
藏曆:2152 木蛇年
⌘ 流亡中的自在 ⌘
第九章:十萬難民
前往達拉薩拉,前半程要乘一夜的火車,後半是坐汽車。一九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我帶著隨員離開莫梭瑞,次日抵達西馬查巴德許的巴丹庫特車站。下了火車的那段旅程我還歷歷在目。車行大約一小時,我看見遠方積滿皚皚白雪的高峰,就在我們的正前方。一路上經過印度最美的鄉野---蔥綠的田野中點綴著樹木,遍地圍滿色彩繽紛的野花。三小時後,我們抵達達拉薩拉市中心,我下了轎車,改搭吉普車,我的住所就在數哩外的麥克雷德甘吉村。
一路山徑陡峭,行來驚險重重,令我憶起拉薩近郊某些地方。有時從山路下望,只見深達數千尺的峭壁。麥克雷德甘吉村在距我的新家一哩處,搭建了一座全新的竹製牌樓,橫楣上以金漆大書『歡迎』字樣。我的新家稱為史瓦格西蘭姆,在英國統治時代則名叫海克羅夫邸,當時是師長的住宅。房子四周有樹林,面積不大,但周圍又加蓋了若干座不相連的小屋,其中有一間是廚房,還有三間供我的隨員居住。雖然盡可以再擴建,但比起我們習慣的生活,房間實在太少了。不過我對於終於能安定下來,已十分感激。 我們抵達時,時間已不早,所以看到的不多。次日清晨,我醒來就听見這一帶特產的一種鳥兒的鳴聲,叫聲像是『卡拉啾,卡拉啾』。我向窗外逡巡,卻看不見的影踪,只見一片宏偉壯麗的山巒。 整體而言,達蘭薩拉的生活相當愉快,只有昆德林因念念不忘莫梭瑞的牛奶滋味,數年前又搬回那兒。達蘭薩拉地區唯一的缺點是多雨,該區降雨量,名列全印第二位。起初這裡的藏人還不上百人,但現在難民人數已超過五千。我們只有一兩次真正考慮要遷移,最近一次是數年前,因為一場大地震摧毀了幾棟建築物而起。大家說,再住下去會有危險。我們沒有離開,是因為這一帶地震活動頻繁,但通常都很輕微。最近的一次重大地震災難發生於一九○五年,當時英國人把這地方當作避暑勝地,地震震垮了他們的教堂尖塔。由此可知,大規模震災殊為少見。何況,從實際的觀點考慮,再搬家也非常困難。 正如在柏拉屋一樣,我跟母親同住在新家裡,還有兩頭最近別人送我的拉薩犬。人人都喜歡這兩頭狗,它們個性分明。我為較大的一頭取名桑吉,我常覺得他前世一定是個和尚,或許就是在西藏飢荒中死去的多名和尚之一。我這麽說是因為一方面對異性毫不感興趣“另一方面,它最喜歡的就是食物:即使吃飽了,它也還有辦法再吃。同時,對我極為忠心。 另一隻狗名叫大西,性情迥然不同,雖然體型較小,卻更為勇敢。它是聖母峰登山專家天津挪格送給我的,或許原因就在此。我記得它有次生病,必須打針。打過一針後就怕了,以後每次獸醫來,都必須由兩個人控制住它,才能順利的注射。其間,大西不斷咆哮怒吼,因此獸醫一辦完事就得趕快離開。獸醫走後,我們才能把狗放開,它會立刻滿屋子亂嗅,搜尋那倒霉的傢伙。不過它其實應了『會叫的狗不咬人』那句俗語,因為它的下顎骨重疊,根本無法囓咬任何東西。 遷往達蘭薩拉時,與我同行的有一位印度政府的連絡官奈爾先生,和若干印度軍方的侍衛。我跟奈爾先生處得非常好,他志願教我英文。我早已了解英文的重要性,並安排天津秋吉到大吉嶺的北點英文學校就讀。我在莫梭瑞時就已開始學英文,印度政府很慷慨的派專人固定來為我上課,每週二或三次;但當時我不太願意學,經常找籍口不上課,所以沒什麽進步。現在我卻很樂意跟我的新連絡官合作,在他的指導下大有精進,不過他要求我的大量作文作業,我還是沒什麽興趣。兩年後他奉派別處任職,我覺得很遺憾。 這以後,我的英文課就較不正式。很多其他人,包括若干西藏人在內,幫助過我,可是我懷疑我現在的英文比二十五年前好。每次出國,我都痛苦的被提醒這回事,想到我不曾把握機會努力學習,常令我羞愧莫名。 住達蘭薩拉的最初幾年,除了學英文,我也專心致志於宗教研究。我從溫習少年時代讀過的許多藏文經典開始,同時,我也研習其他宗教派的大師處於顛沛困頓下的教誨。儘管離成佛的境界還很遙遠,但我目前沒有工作的壓力,反而完成不少工作。不幸,時間不夠用,很快就成為我在這面求進步的重大障礙。但我可以說,我任何心靈上的長進,跟我投入的努力完全不成比例。 抵達達蘭薩拉兩週之內,我就設立了第一所西藏難民子女的育幼院,它位於一所原本遭廢棄的小屋,由印度政府租給我們收容新來者當中日益增加的孤兒。我任命我的姊姊澤仁多瑪經營這所育幼院。第一批五十名兒童來到時,已幾乎沒有多少容身之地,但比起後到的人,他們已經過得很豪華,因為年底時,人數已增為十倍,而且還不斷在增加。有一陣子,一百二十人合住一間寢室,每張床必須睡五到六個人,大家橫著躺才勉強擠得下。雖然環境這麽苦,但我每此時去探望姊姊,看見她的新家族擴大,都覺得滿心歡喜。因為這些孩子雖然失去了父母,卻依然充滿歡笑,彷彿在嘲笑身處的困境。 我姊姊果然極具領導能力。她永遠不沮喪。她是個強壯的女人,而且賦有家傳的脾氣,她要求非常嚴格,但心地極為仁慈而富幽默感。她在困難中給我的幫助可說是無法衡量。她早年是個單純的村姑,沒有受過任何教育,兒時大部分時間都在幫我母親料理家務。她的任勞任怨,加上勇往直前的性格,是她成為領袖的基本條件。 不過,很快便顯而易見的是,我們跟印度政府都沒有足夠的財力照顧我們所有的孤兒。我只好決定,如果可能的話,至少把他們之中的一部分交由海外人士認養。所以我跟一位瑞士朋友艾希曼醫生連絡,請他就這構想的可行性。瑞士在我看來很理想,這是個小國家,通訊發達,更何況還有跟故鄉類似的重疊山巒。 瑞士政府從一開始就很合作,表示可立刻接納兩百個孩子。更有甚者,她同意設法安排,使這些孩子在收養他們的一般瑞士家庭中,盡可能保存追尋原來的西藏文化與認同感的機會。 第一批孩子之後還有其他批,後來又有個計劃,不但讓較年長的學生到瑞士政府救濟,但我仍然允許一千名成年難民遷往移民。我們的境況改善後,不必再請求瑞士政府救濟,但我仍然對他們為我的同胞所作的一切深懷感激。 抵達達蘭薩拉後不久,我親身接觸到國家法學委員會的成員,前一年他們曾帶給我們很大的鼓舞。他們要我提供證據給該會的法律調查小組,我欣然從命。這些調查的結果一九六○年八月於日內瓦出版。法學委員會再次證實西藏的觀點,它在報告中指出:中共觸犯了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rs)的十六項條款,並在西藏進行種族滅絕的罪行。他們也詳細列舉了若干我已經談過的卑鄙暴行。 在實際的層次上,我跟該委員會討論,學會了一件非常有用的事。它有位成員,我猜是位英國人,問我有沒有專人監聽北京的廣播。我答稱沒有,他有點驚訝,並詳細說明為什麽有必要聽清楚中共說些什麽。我們沒有想到這事,實在太缺乏經驗了。在我們看來,北京電台只會散佈謊言與宣傳。我們不懂得從廣播中可了解中共的想法動態。但我能領會這麽做的道理,並立刻下領噶廈組成監聽小組---他們的繼任者到今天仍在執行這項任務。 一九六○年一整年,我都繼續致力於改革西藏的行政制度,並且跟噶廈其他人共同努力,展開全面民主化的艱難歷程。九月二日,我成立了西藏人民代表委員會,這是政府的最高立法機關,代表由西藏烏昌、安多與康省三地經自由選舉產生。西藏佛教的主要宗派也同樣擁有議席。後來,古老的苯教信徒也包括在內。這個現在人稱西藏人民代表大會的委員會的作用與國會相同。它的成員每月要跟噶廈及各部會首長開會一次。特殊情況下,它要跟由部會首長及噶廈成員組成的全國工作委員會開會。現在噶廈的成員也不再由我指派,而是從選舉產生。人民代表投票通過的事項都必須依照決議執行。 一開始,這些新安排都不是盡如人意。這些變化對西藏人而言太過突兀,有些人甚至認為,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在實行真正的共產主義!三十年後,我們仍面臨很多問題,但事態不斷在改變與改進。我們當然已領先留在中國的兄弟姐妹,中共可以跟我們學習很多事。撰寫這本書期間,西藏流亡政府正在實施進一步推動民主的新措施。 伴我流亡的若干較年長的官員,最初覺得無法接受這些改變。但大部分人都認清改革的必要,表現得非常熱心努力。我將永遠感謝他們。 最初幾年,我個人雖然過得還算舒適,但大多數政府官員生活卻都很苦。他們即使年紀很大,也被迫過著貧困的生活,有些人竟住在牛棚裡。但他們安之若素,從不抱怨。雖然也有人觀念較保守,不能同意我的領導方向,但是那段黑暗的日子裡,每個人都有貢獻。他們欣然面對困境,盡力幫助流離失所的同胞建立新生活,絲毫不以個人得失為念。當時他們的月薪還不到三英鎊,憑他們所受的教育,到別處覓職,收入絕對會好得多。 更何況那時候的行政工作一點也不輕鬆。人際的歧異和無謂的爭執本來就無可避免,因為這都是人性的一部分。但整個而言。每個人都能熱忱而無私的為他人謀福利。 從一開始,我另一個重要目標就是保存和延續我們的宗教。沒有宗教,我們的文化泉源就會枯涸。最初,印度政府同意在不丹邊界附近的布哈杜爾戰俘營舊址,成立一個由三百名僧人組成的學術社區。但經我們說明佛教須仰賴高水準學術後,終於說服他們增加經費,資助一千五百名各教派的僧人。流亡出來的六千多名僧人中,最年輕與最有能力者加起來就這麽多,其中有多位經驗豐富的上師。 不幸的是,布哈杜爾的情況很惡劣。天氣又熱又潮濕,疾病猖獗。口糧必須自遠方運來,使問題更形惡化,往往運到時已經不堪食用。不到幾個月,已有數百名學者僧人羅患肺結核。儘管如此,他們還是努力工作和研究,直到自己能活動為止。我很遺憾無法親自到那兒去,只有靠寫信和寄錄音帶為他們打氣。雖然這也多少發揮了作用,雖然營區的問題並未改善,但生存下來的人卻成為一個個活力充沛的僧院社區的核心分子。 不用說,我們早年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缺錢。在教育和移民計劃上,因為有慷慨的印度政府和海外各志願機構資助,倒還不構成問題。但在行政方面,我覺得請別人幫助不大恰當。靠每個人每個月樂捐兩盧比的自由稅,再加上受薪人員每個月同樣是樂捐的百分之二所得稅,實在做不了什麽。好在天津早在一九五○年就有先見之明,在錫金存了一批寶物,至今仍在,它成為我們的生命。 最初,我打算把這批寶物賣給印度政府,這是尼赫魯主動提出的建議。但我的顧問堅持在公開市場出售,他們確信這麽做能換得更多的錢。最後我們在加爾各答拍賣,得款相當於幣值八百萬美元,在我看來簡直是個天文數字。 這筆錢用於投資多種事業,包括一家鋼管工廠,一家紙廠的相關企業,以及其他所謂保證賺大錢的事業。不幸的是,這些幫助我們適用這筆寶貴資金的計劃,不久被宣告失敗。很遺憾,很多表面上要幫助我們的人,其實對於幫助他們自己更感興趣,我們大部分資金就這樣失去。去結堪布的高瞻遠矚,大多數被浪費了。 最後只搶救到不及一百萬美金的錢----一九六四年成立達賴喇嘛慈善信託基金。其實我自己對這樣的結局並不太難過。回想起來,這批寶物很顯然該屬於全西藏人民。而不是我們逃出來的少數人的財產,因此我們也無權獨享,這是宿命。我聯想到林仁波切立下的先例,我們離開拉薩那晚,他把最喜歡的手錶留下,他覺得流亡就代表放棄保有這只表的權利。我現在明白他這種看法是正確的。 至於我個人的財務,過去有兩個部門專司處理,一九五九年起才裁減為一個,稱為內務辦公室(Private Office),處理我一切收入與開銷,包括印度政府以薪俸方式支付,每日二十盧比的零用金:略高於美金一元。理論上,這筆錢支應我的衣食費用。正如過去一樣,我從不直接接觸錢,這樣或許比較好,因為我雖然從小對小錢很吝嗇,但我一直擔心自己生性揮霍。不過,我還是有權決定個人得到的錢(例如諾貝爾獎金)該怎麽運用。 達蘭薩拉的第一個夏季,我有一些休閒的時光,大多數的傍晚打羽毛球(我經常不穿袈裟)。冬季嚴寒,我們玩雪也非常愉快。我的母親和姊姊年紀雖已不輕,打起雪球仗來卻比誰都興高彩烈。 還有一種比較耗費體力的休閒活動,就是攀登附近的達拉達山,最高峰海拔七千多英尺。我一向愛山,有次,我率領一隊西藏侍衛攀到極高的地方,到了山頂,大家都很疲倦,我提議休息一會兒。大家喘著氣坐觀美景的時候,我發現遠處有個山區土著正盯著我們看,他們都長得瘦小黧黑,看似很狡猾。他看了一會兒,忽然坐在一塊像是木板的東西上,很快就沿著山邊滑下去了。我驚訝的看著他的身影一轉瞬就化為一個小黑點,消失在數千英尺下,就提議我們也模仿他的方式下山。 有人拿出一條繩索,我們十個人都綁成一串。然後我們各自坐在木板或扁平的石塊上,急速溜下山坡。非常好玩,但也非常危險。一路顛簸得很厲害,我們在一片雪堆裡撞成一團,撞得滿身青紫,好在沒有人受傷。但此後我就發現,我很多隨員都不大願意離開我們的基地了。尤其我的侍衛,每當我宣布新的探險計劃,都表現得非常猶豫。 這個階段,我其餘空閒的時間都用於跟一位英國作家大衛.霍華恩(David Howareh)合作一本書《吾土吾民》(My Land and My Peopie),書中我初次敘述我的一生。 一九六一年,我們政府出版了一份西藏憲法草案綱領,請所有西藏人提出批評與建議。我們得到很多反應,主要是針對有關達賴喇嘛一職的重要條款,為了正式脫離神治,展開民主政治,我加入一條規定:只要國民大會三分之二票數通過,就可解除達賴喇嘛職權。很不幸,『達賴喇嘛可以罷免』這種念頭,令很多西藏人大吃一驚。我必須對他們說明,民主完全符合佛教的原則,而且幾近專制的堅持保留這項條款。 那年的年初,除了再次探望流浪難民,我也第一次拜訪了拜拉庫普的新屯墾區。我一到就發現,所有的屯墾者都又黑又瘦,我也立刻了解他們如此悲觀的原因。營區位於邊緣,只有幾個帳篷,雖然鄉野風光仍跟我初來時記憶中一樣美麗,但土地本身看來並不肥沃。更有甚者,燃燒林木的熱氣,加上熱的陽光,幾乎令人無法忍受。 屯墾者特別為我用竹籬和帆布搭了一個帳篷,但儘管搭得很好,也還是擋不住墾荒掀起的大片砂塵。這地區每天都籠罩在濃煙和煤灰當中,晚間煙和灰降落下來,透過所有的縫隙,早晨醒來,身上就是一層薄薄的黑灰。這些因素導致土氣非常低落,但我除了口頭的鼓勵,實在幫不上什麽忙。我告訴他們絕不能放棄希望,並向他們保證有朝一日我們一定會克服一切難關,再次興旺起來,其實我自己都沒多大信心。但幸好他們相信我說的每一個字,而他們的情況也真的一點一點的改善了。 多虧印度好幾個省份慷慨援助,我們才得以在一九六○年代早期,建立了二十多個屯墾區,使大家逐漸不需要再四處流浪。目前十萬難民中,只剩下數百人仍然過著四處流浪的生活,而且這是出於他們自己的抉擇。 因為劃給我們的土地一半以上位於印度南部,那兒的氣候比北方炎熱得多,所以我規定,草創階段只能派身體最強壯的人前去。儘管如此,因中署與熱衰竭死亡的人數多得令我懷疑是否該接受位於熱帶的土地。不過,我相信我的同胞早晚會適應的。正如他們相信我,我也對他們有信心。 我拜訪各營區時,往往必須安慰難民。想到遠離故鄉,今生今世可能再也見不到冰雪,更不要說我們心愛的山巒,真令他們悲從中來。我試著使他們不去想過去,我告訴他們,西藏的未來就靠我們難民。為了保存我們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必須建立強大的社區。談到教育與婚姻制度的重要性,雖然一個和尚對後者的了解很有限。我勸婦女盡可能嫁西藏男人,這樣他們的孩子才會也是西藏人。 大多數屯墾區建於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五年之間。這期間我盡可能到各處巡視。雖然我從不考慮失敗,但有時問題卻似乎不可能克服。例如在馬哈拉許德拉省的班德哈拉,第一批屯墾者於春天到達,剛好是炎熱季節開始前。不到幾個星期,就有一百人(五分之一的人數)死於酷熱。我第一次去探望他們時,他們含著眼淚求我把他們疏散較涼爽的地區。我只能解釋給他們聽,他們到的時間是最壞的時間,現在最惡劣的時機已經熬過去了。他們應該已適應當地人的生活方式,學會利用環境。我勸他們再試一年,如果次年冬季我再來時,他們還是無法成功,我保證安排他們遷往別處。 結果此後事情就變得很順利。十二個月後我回去,發現他們已大有改進。我跟營區的領袖見面時說:『原來你們沒死光阿! 』他笑著說,一切都正如我們所料。不過我必須說明,雖然這個社區後來都發展得很好,但由於炎熱的問題,它的人數始終只有七百多人。原來我們分到三千英畝土地,預定每名屯民可分配一英畝,但由於人數不足,我們又喪失了兩千三百英畝,這些土地被分配給其他難民但他們也同樣撐不久。 屯墾計劃的一大困難在於,雖然我們對大多數障礙都早有準備,但還是會出現意料之外的問題。例如有個地方遭野豬野象肆虐,它們不但破壞莊稼,而且狂性大發時還撞倒數棟房舍,殺害了好幾個人。 我記得有位住在那兒的老喇嘛要我為他們禱告求保佑,但提到像這個字時,必須用梵文取代。在梵文中,這個字 hathi 原意為珍貴的動物,神話中像是慈善的象徵。我懂他的意思,但這個字眼這種用法卻令我十分驚訝。我想這位老喇嘛心目中認為,真正的象應該是一種仁慈的動物。 好幾年以後,我在瑞士參觀一處農場,發現他們有通電的圍籬。我問導遊這是否撐得住大象。他驚訝的回答,如果電壓夠高,應該沒有什麽不可以。所以我就送了一套這種裝備到有像災的屯墾區。 但並非所有的問題這麽具體。有時問題出在傳統文化使我們無法適應新環境。我記得很清楚,我第一次到拜拉庫普時,屯民非常擔心放火燒林會害死林中的小動物與昆蟲。佛教徒最忌殺生,甚至有幾位屯民來找我,提議中止這項工作。 有些跟海外救濟機構合作的計劃也因這個緣故而告失敗。例如養雞場和養豬場的計劃都不曾成功過。西藏人生活再苦,也不願從事用動物血肉生產食物的行業。有些外國人覺得這很可笑,他們指出,西藏人願意吃肉,卻不願自行生產,這種態度相當不合理。 除此之外,在外國組織協助下進行的其他計劃,大部分都很成功,我們的友人對結果也頗為滿意。 獲得工業先進國家的人民免費提供我們支持的經驗,更堅定了我對宇宙責任(Universal Responsibility)的基本信念,在我看來,它是人類進步之鑰。沒有宇宙責任的觀念,世界的發展永遠不會平等。許多人了解我們不能孤立於世界之外,大家應以兄弟姐妹相待的道理,全人類共同的進步才有可能實現。 有幾位為難民奉獻人生的外國人,最令我難忘。其中之一是來自波瀾的猶太人莫理士.弗利德曼(Maurice Friendmann),我一九五六年第一次見到他和一位波瀾的畫家朋友媯瑪.戴薇(Uma Devi)。他們分別來到印度,追求印度式的生活。我們流亡來此時,他們是最先對我們伸出援手的人。 弗利德曼這時年紀已相當老,身體健康也不好。他駝背,鏡片極厚的眼鏡說明他視力不佳,但他有雙透視人心的藍眼睛和敏銳的思考力。他有時會頑固的堅持一項根本不可能成功的計劃,令人惱火。但整個而言,他提供的建議,尤其有關建立兒童之家方面,都極具價值。戴薇比弗利德曼更傾向致力於靈性的修養,但年紀也不小,她把餘年都用餘為我的同胞服務。 還有一位重要人物是為瑞士紅十字會工作的魯提(Lu thi),西藏人稱他為『爸爸』(Pala)。他擁有無比的熱情與活力,是一流的領導人才,替他工作的人都必須全力以赴,任勞任怨。一向悠遊自在慣了的西藏人都覺得他的作風令人無法忍受,我知道有不少人私下怨言,但事實上他還是深受愛戴。我珍惜對他,以及其他像他這樣的人的回憶,他們都全心全意的為我的同胞無私地奉獻。 對西藏人而言,一九六○年代早期最重要的事件莫過於一九六二年的中印戰爭。戰事開始時,我當然很難過,但難過之中還夾雜著恐懼。當時屯墾計劃才剛剛起步,若干流浪營區距戰門地點極近,十分危險,拉達克(Ladakh)與NEFA甚至被迫關閉。我的一部分同胞因而被迫第二度成為難民。更糟的是,我們的恩人印度人也受到駐紮西藏的中共士兵的侮辱。 幸好戰爭為時不久,但雙方都死傷慘重,各有勝負。尼赫魯反省他對中共的政策,不得不承認印度一直『生活在自塑的空中樓閣中』。 他畢生夢想解放全亞洲,使每個國家和諧共存。但現在證明,簽署已十年的班察希爾備忘錄只是一張廢紙,這位古道熱腸的政壇領袖維繫它的努力都歸於徒然。 直到尼赫魯一九六四年去世為止。我一直跟他保持連絡。他一直很關心西藏難民的困境,尤其兒童的教育問題最得他重視。很多人說,中印戰爭大大傷了他的心,我想這話沒錯。那年五月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我走進室內,就覺得他心情極其消沉。他剛中過一次風,身體很弱,形容焦悴地坐在靠椅上,背後墊著枕頭。我注意到,除了身體方面的不適,他也有很大的心理壓力。我們這次晤面的時間很短,我帶著沉重的心情告辭。 那天後來他前去德拉屯,我到機場送行,並且遇見他的女兒 英德拉. 甘地夫人,一九五四年,她伴隨父親訪問北京時,我就認識她了(最初我誤以為她是尼赫魯的妻子)。我告訴她,我對他父親身體不適感到很遺憾。我甚至說,我恐怕再也見不到他了。 結果真是如此,他不到一周之內就去世了。雖然我無法參加他的火葬禮,但他的骨灰灑在阿拉哈巴德(Allahabad)三河匯流處時,我也在場。這對我而言是極大的殊榮,使我與他的家人更親近。我見到英德拉。儀式結束後,她走過來,直視著我的眼睛:『你早就知道了! 』 |
| © The Office of His Holiness the 14th Dalai Lama. e-mail: service@dalailamaworld.co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