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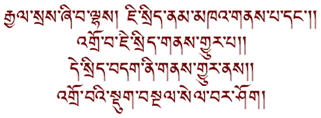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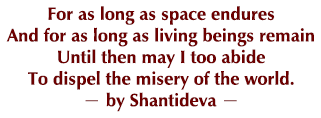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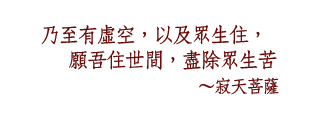 達賴喇嘛格言
不管一個人是否信仰宗教,不管一個人是信這個宗教或那個宗教,我們人生的確切目的就是快樂,人生的確切動機即是追尋快樂。
相關連結
|
藏曆:2152 木蛇年
⌘ 流亡中的自在 ⌘
第八章:風雨飄搖的歲月
印度邊境的少數守軍肯定是看到一副可憐的景象---八十位西藏難民經過長途跋涉,身體疲憊不堪,內心也因為歷經嚴峻考驗而沮喪。但是,我還是高興,因為有一位我在二年前訪問印度時認識的官員在那里和我們會面。他對我說,他奉命護送我去旁地拉(Bomtila)安頓,旁地拉是個大城鎮,距離此地一星期多的路程。
最後,在逃離拉薩三星期後,我們到達旁地拉,這時間漫長得像過了一劫。當我到達時,我的老連絡官和翻譯,梅農先生(Mr. Menon)和蘇南.托結.卡日(Sonnam Topgyal Kazi)早就在那兒等後,其中一位呈交我一份印度首相打來的電報: 我的同僚們和我歡迎你,並致侯你安全抵達印度。我們很高興能提供必要的設備給你、你的家族和隨員,以便安住在印度。對你保持極高敬意的印度人民毫無疑問地會依照傳統,給予閣下應有的尊重。 願慈悲關照你 我在旁地拉停留了十天,受到當地地區委員會家族的悉心照顧,離開時,我的痢疾已經完全好了。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以前,我乘坐吉普車前往一處叫腳山(Foothills)的公路營(Roadcamp),那裡早就有一小隊儀隊排列在替代地毯的帆布地毯兩旁,地毯一直鋪到公路營監督的房子---我那天早上暫用的基地。我就在房子裡面吃了一頓有新鮮香蕉的早餐,但是我吃得太多了,消化系統出了問題,結果不得不由梅農先生代表我向大家簡報印度政府的安排。 當天中午我就被帶到德普(Tezpur),從那兒開始了前往莫梭瑞(Mossoorie)的旅途,莫梭瑞是一個距離德里不遠的山站,在那兒早就為我準備好了一幢房子。印度政府也為了我們這段一千五百英里的旅程特別準備了一列火車。 我離開腳山的房子,準備坐上一輛大的紅色車子之際,我注意到有一大群拿著攝影機的人,有人告訴我,這些人是國際新聞界的採訪記者,他們是來採訪『世紀故事』。入城時,我會看見更多的採訪記者。 我們到達達普時,我被直接帶到『巡迴宮廳』(CiruitHouse)。那裡早就有數百件消息、電報、信件等著我。這些來自全世界的問侯和關心。有一段時間,我的心中充滿感激,幾乎忘掉眼前的各種危機。最最迫切要作的事,我覺得,就是準備一份坦白、謹慎、措詞溫和的大綱,這些歷史事實,我在前面幾章已經說明過了。在辦完這件事之後,我吃了一頓簡單的午餐,然後準備搭火車,這班火車在下午一點就應該要開動。 在路上,成百成千的民眾緊緊地包圍著我的車隊,揮手、歡呼。這種情況從我啟程直到莫梭瑞,整段旅程都持續不斷。有些地方,甚至不得不驅離鐵軌上的那些善男信女。消息在鐵路沿線的村落不脛而走,似乎沒有人不知道我就坐在火車上。數以千計以上的人們跑出來,並且高喊:Dalai Lama Ki Fai! Dalai Lama Zinda bad! (向達賴喇嘛致敬!祝達賴喇嘛萬壽無疆!)這種場面令人非常感動。在路過沿線的三個主要城市希利古瑞(Siliguri)、班納瑞斯(Benares)和路克諾(Lucknow)時,我不得不離開車廂,答謝那些自發前來、散花歡迎我的廣大印度人民。這趟旅程就像一場非常的夢。回想起這趟旅程,我非常感謝當時印度人民向我表達的殷殷善意。 經過許多天的旅程後,火車最後到達得拉屯(Dehra Dun)站。在那兒又有盛大的歡迎等著我。我從德拉屯坐車前往莫梭瑞,這段路程大約花了一個鐘頭。我被帶到拍拉屋(BirlaHouse),這是印度工業領袖家族的居所。印度政府早已為我準備好了,我可以居停在那兒,直到我作好了長期計劃。而事實上,我以此處作為行館,達一年之久。 我到達柏拉屋翌日,聽到新中國新聞社報導,暗示因為我在達普所作的聲明是第三者所寫,所以不是真的;它接著又聲稱我已經被綁架了,並且遭叛徒脅迫,說我的聲明是粗製濫制的文件、意理不通,充滿了謊言和漏洞。這份中國版的故事,形容西藏人民的抗暴是由反動的上層派系所組織的;然而,他們又說,由於西藏愛國僧侶的幫助,中共人民解放軍徹底地粉碎了反革命。基本上,這是因為西藏人民是愛國的、支持中央人民政府、熱愛人民解放軍,並且反對帝國主義和叛徒。因此我又發表另一篇公報,堅定地指出該聲明是由我所授權發布的。 四月二十四日,尼赫魯班智達親自來到莫梭瑞。我們透過一位譯員會談了四個鐘頭。一開始我告訴他回到西藏之後,所發生的每一件事---我提醒他,這些作為大部分是出諸他的堅持。我繼續說,我已經照著他所建議的去作了,並且和中共公正、誠實地交涉,批評他們那裡需要、努力地去遵守十七點協議。然後,我接著說明我原本並不是尋求印度人的殷勤款待;相反地,我曾經要在隆次宗(Lhuntse Dzong)建立政府。只有從拉薩傳來的消息曾改變我的主意。到了這時候,尼赫魯變得更生氣,『即使你已經成立政府,印度政府也不會承認它。 』他說。我開始認為,尼赫魯把我當成一個需要常常叱責的年輕人。 在我們會談的其他時間,尼赫魯捶打桌子:這怎麽會這樣?他輕蔑地一次、二次逼問。雖然他愈來愈像是一個恃強凌弱的人,但我仍然繼續說。最後我非常堅定地告訴他,我關切的主要有兩點:我決定贏得西藏的獨立,但是眼前當務之急是停止流血。這時候,他再也無法控制自己。 『這是不可能! 』他以充滿情緒的聲調對我說:『你說你要獨立,同時你又說不要流血。不可能! 』他說話時,下唇憤怒地顫動著。 我開始了解尼赫魯首相發現他自己正處於一種微妙而又困窘的形勢。在印度國會裡,隨著我逃離拉薩的消息,帶來了另一場有關西藏問題的激烈辯論。許多年來直到現在,已經有許多政界人士批評他對這個情勢的處置不當。現在,我似乎看到,他顯示了一種良心不安的徵兆。他曾在一九五七年時,堅持我要返回西藏。 然而就在同時,顯然尼赫魯想要保住印度和中共的友好關係,並且決定堅守班察希爾備忘錄(Panch Sheel Memoranaum)的條款,印度的政治家阿.梨庫立帕拉尼(Acharya Kripalani)這麽形容這個備忘錄:在明知不可卻不得不為的情況下,印度蓋章同意中共摧毀一個文化古國。他的態度相當清楚;印度政府仍然無法考慮和中共政府就西藏人的權利這一問題展開討論。現在,我應該休息,並且不要對最近的將來作任何打算。在未來其他場合所舉行的討論中我們會有機會再談談。聽到了這些話,我開始了解我的未來以及西藏人民的未來比我原先想像的還要更不確定。雙方的會談雖在熱忱氣氛中結束,但是等到尼赫魯首相離去,我心中卻縈繞著深深的失望。 情勢很快地明朗化了,然而,我們要面對比西藏獨立更迫切的問題。我們一到莫梭瑞,就收到報告說大批難民逃抵印度以及不丹。我立刻就派出一些官員把他們安頓在印度政府緊急設置的難民營中。 從這些剛逃出來的難民口中,我知道中共在砲轟諾布林卡宮後,又把砲口對準布達拉宮和大昭寺,屠殺、殺傷了上千的民眾。這兩個地方的建築都被破壞得很嚴重。察克波里醫藥學院被整個破壞無遺。沒有人知道在這場屠殺中有多少人被殺,但是根據西藏自由門士在一九六○年間所擄獲的中共人民解放軍文件顯示:一九五九年五月到一九六○年九月,這段期間有八萬七千人是死於軍事鎮壓(這個數字並不包括那些死於自殺、嚴刑拷打、飢餓的人們)。 結果,成千上萬的西藏人想逃出西藏。許多人死亡,有些人是直接死於中共之手,有些人是死於傷重、營養不良、酷冷、疾病。那些想越過藏印邊境逃離的人,都是在悲慘、為人棄絕的情況下逃出。雖然當他們抵達印度時,有食物及庇護所等著他們,但是殘忍的印度驕陽卻無情地攫走許多人的生命。當時有兩個營區讓這些難民暫住,一個是在莫梭瑞,靠近達普;另一個在哈杜爾(BuxaDuar),該處是大戰時英國的戰俘營,位於不丹邊境的東北方。 這兩個地方的海拔高度都比莫梭瑞的六千英尺低,所以酷熱並未緩和些。在西藏,夏季雖然更熱,但是高海拔的西藏高原空氣非常乾燥;但在印度平原卻是又濕又熱。這種氣候不僅是西藏難民不舒服,也常常造成死亡。一些西藏難民所不知道的各種疾病,就在這新環境中滋生。因此,除了在逃離過程中最常遭遇受傷致死的危險外,西藏難民也面臨酷熱侵襲致死以及疾病的危險,例如肺結核,這種疾病在印度的環境最易流行。許多人都死了。 像我們這些住在莫梭瑞的西藏人被認為是比大多數的西藏人民要幸運得多。因為在柏拉屋裝有電扇,所以我也許是最不受熱罪的人,但是吹電扇也有吹電扇的困擾,我發現如果任其整晚吹拂,會引起消化的毛病。我想起一位在布達拉宮潔役所說的諺語:冬天氣候冷,晚上睡覺裹起來;夏天一到天氣熱,你就忘記了。 我的另一個小發現就是熱天氣會使人多吃水果,天氣冷時就不會有這種慾望。在夏季月份裡,熱浪侵襲西藏難民時,我必須從莫梭瑞下去到平原地帶,因此,我個人感受到這種不舒服滋味的次數有限。 第一次是在六月時,我前往德里拜訪尼赫魯首相,會商有關西藏難民日增的問題。當時已有二萬名西藏難民,而且人數每天都在增加。 我懇求印度政府能將這些新來的難民安頓到氣候不像達普、布哈杜爾那麽濕熱的地方。這些難民穿著長袍子、厚重的靴子逃出西藏,完全不知道即將逼近的熱季。雖然第一批逃出西藏解放者魔手的幾千名西藏難民大多數是男人,許多是來自拉薩以及臨近的地區,稍後開始有整個家族逃出,這些人主要是來自邊境地區,當時中共尚未完全嚴密控制。 我對尼赫魯說,我深信如果這些西藏難民留置在那裡,大部分都會死亡。起初,他顯現一些被激怒的徵象。尼赫魯說我要求得太多了。我必須記住印度還是個貧窮、發展中的國家。但是很快地他的人性本能又佔上風了。噶廈現前曾和印度官員商討僱用難民在印度東北公路營築路的計劃,現在尼赫魯說他希望這件計劃盡可能地付諸實行。這樣一來使得難民能賺得日常生活所需,同時他們也能到氣候較適宜的地方。 接著,他談到有關西藏未來的教育問題,很快地他就表現得很熱心,最後,他對這個問題的高度興趣,顯示他好像把這件事當成是他個人的責任。他說,因為到目前為止,在可預見的將來,他把我們當成是印度的客人,我們的兒童們將會是我們最珍貴的資源。我們應該好好教育這些孩子。為了保存西藏文化,我們應該為孩子們設立特別的學校。在印度教育部中應該設立獨立的西藏教育學會。他補充說,印度政府會負擔設立這些學校的所有經費(直到今天,印度政府仍然繼續資助大部分的西藏教育工作計劃)。 最後他提醒我,這些孩子應該接受完整的西藏歷史和文化的知識,這件事非常重要;另外這些孩子也務必要跟上現代世界的腳步。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為了這個緣故,他說,我們應該採用英語來教學,因為『英語是未來的國際通用語言』。我們會談之後就共進午餐。午餐後,尼赫魯說他會召見教育部長師利馬博士(Dr.Shrimali),使得我們有機會繼續會商。在那個中午,尼赫魯首相告訴我,印度政府會在今天就宣布成立西藏教育學會。我對這個迅速的回應感到非常振奮。 從許多年來到今天,印度人民和政府已經給予我們西藏難民非常多的幫助,包括經濟上的援助以及其他許多方面的幫助----儘管印度自己在經濟上有極大的困難。我懷疑是否有其他的難民會被其居停國如此地善待。這種情誼我永遠銘感心中。當西藏難民不得不要求更多的金錢援助時,成千上萬的印度兒童甚至無法接受基本教育。 雖然實情如此,但是只有印度才有權利來援助我們。因為佛教是從印度傳到西藏,此外伴隨佛教傳入,還有許多其他重要的文化影響。因此我心中毫無疑問地認為印度比中國更有理由聲稱領有西藏主權。中國對西藏只有過些微的影響力。我常常把印度和西藏的關係比喻成老師和弟子的關係。當弟子有困難時,幫助弟子就是老師的責任。 另外許多外國的救濟組織對西藏難民的慷慨援助也不在印度政府之下。他們所提供的許多援助都是很實際的,尤其在保健以及教育方面。他們所協助設立的手工藝以及其他工作中心,也提供了許多有意義的工作機會。首現是在大吉嶺以及達爾荷西(Dalhousie)設立了織造毛毯的工作坊(大吉嶺是在印度、尼泊爾邊境上的高山製茶城鎮,達爾荷西距離達蘭薩拉不遠。這兩個地方的工作坊都是印度政府在一九五九年底設立的。以這兩個中心為模型,許多其他類似的中心也在海外機構的資助下設立某些機構至到今天仍繼續支持。現在,經過了這麽多年,每一個從一開始參與我們流亡生涯的救濟組織都對西藏難民在他們指導下的進步,感到非常滿意。 西藏難民對這些友人所提供的援助作了積極的回應,就是我們西藏人表達無比感激的最佳方式。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捐贈給這些外國機構的錢常常都是來自那些金錢原本就不充裕的善心人士。在拜訪德里之後我就回到莫梭瑞。我覺得打破沉默的時機已經成熟了。六月二十日,我舉行記者招待會。在莫梭瑞仍然有許多新聞記者在等著我說些話。雖然『故事』發生至今已逾二個月了,一共有一百三十位記者與會,他們來自世界各地。 首先我正式地再一次否認了十七點協議。我解釋說,因為中共撕毀了它自己的協議,所以沒有任何合法的基礎來承認十七點協議。接著我詳細說明我的原始簡短聲明,並且指證歷歷的控訴中共如何惡毒、殘暴地對待西藏人。我確定人們會了解我所說的話較接近真理,中共所說的是令人無法相信的謊話。雖然我的最新聲明得到廣大的迴響,但是我低估了中共政府在搞公共關係上所能動員的力量。或者也許我高估了人類面對真理的意願。我相信這個特質首先在文化大革命時展現了,接著是中共武力鎮壓天安門的事實透過電視熒幕傳遍世界,全世界都看到中共是如何虛假、殘酷。 當然傍晚,印度政府發布一則官方公報:印度政府不承認達賴喇嘛的流亡政府。一開始我有些驚愕,接著是覺得這份公報傷了我的心。我完全了解印度政府在政治上並不支持我們,但是像這樣子的撇清似乎是不必要的。然而,我受到傷害的感情很快地被無比的感激所取代,因為我看到,真的第一次看到,『民主』的真正意義。印度政府雖然強烈反對我的看法,但是並沒有阻止我表達的看法,更沒有不准我堅持己見。 同樣地,德里方面也沒有乾擾我和日益增加的難民過自己的生活。為了順應大眾要求,我開始每星期在柏拉屋的庭園接見民眾。這讓我有機會見到不同的人,並且向他們敘說西藏的真實情況。這也幫助我著手取消許多繁瑣的禮儀,這些禮儀把我和西藏人民隔絕得這麽遠。我心中強烈地感覺我們不該再緊緊抱著老舊的習慣不放,這些已經落伍了。我常常提醒西藏人,我們現在是難民。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堅持所有的禮節都要研商簡化,並且釐清,因為我不想再讓西藏人對我行那些大禮。我覺得這非常重要,尤其和外國人來往時。如果他們發現真正的價值,這些外國人更回應它。保持距離就很容易使人遠離。所以我決定完全公開,把每一件事都公開,不要躲在禮節後面。我希望以這種方式使人們視我為凡人。 我規定我接見任何人時,他和她應該坐在和我相同高度的椅子,而不是傳統禮節中的我坐在高位,覲見者坐在較低的位子。剛開始我發現這種作法相當困難,而我也沒有多大的自信,但是從那時起慢慢有些進展。雖然某些長老們有些疑懼,但是我相信只有剛從西藏逃出來的人才會對新的規矩不知所措,他們並不知道達賴喇嘛已經不再以他們所習慣的方式生活了。 在柏拉屋的生活處處非常不利於禮儀。它既不特別堂皇,地方也不大,有時候還頗擁擠。我和母親以及管家共住,其他隨從、官員則住在附近。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能常常見到母親。能陪伴母親,我非常高興。 除了簡化禮節,我們的悲劇也給我機會大幅簡化我個人的生活。在拉薩時,我擁有許多不太有用的財物,但是我很難把它們丟掉。現在我幾乎一無所有,但是只要有助於我的西藏難民同胞,我發現我更能把送給我的東西布施。 在行政方面,我也能作激烈的改革。例如我在這時候增設新的政府部門,這些部門包括情報、教育、重建、安全、宗教事務以及經濟事務等辦公室。我也特別鼓勵女性參與政府。我提醒人們,重要官位的升遷不該以性別為準,應該要看品德和才能。我前面提過,在西藏社會中,女人一向扮演重要角色;今天,有許多女性在西藏流亡政府裡位居要津。 我在九月間回到德里。當時,我對西藏難民的事,心懷較樂觀的看法。難民的人數已經增加到幾乎三萬人,但是尼赫魯信守諾言,許多西藏難民也已經被轉送到北印山上的各個公路營區。現在我主要的目標就是要在聯合國提出西藏獨立權的問題。於是我又再度拜訪尼赫魯首相。我們花了一些時間討論將新近抵印度的難民轉送到南印度的新方案。尼赫魯已經發函詢問印度許多州的首長,是否能準備提供土地給西藏難民。 我聽到不只一州提供土地時,我表示非常滿意;之後,我提出在聯合國舉行聽證會的計劃。就在這時,尼赫魯露出憤怒的樣子。因為西藏和中共都不是會員國,他說看情形我的成功率非常渺茫。而且即使我辦到了,效力也不大。我告訴他,我知道這些困難,我這麽做只是想讓世人記得西藏。不讓世人忘掉西藏人的悲慘遭遇是非常重要的。 『使西藏問題繼續凸顯下去,並不是靠聯合國,而是要靠下一代的適當教育。但是這完全要看你自己。你生活在一個自由國度裡。 』他說。 我已經寫信給許多國家的政府,現在我會見了一些國家的大使。我發現這是一樁非常難堪的考驗。當時我只有廿四歲,我和高級官員交涉的經驗十分有限,我只有訪問中國時得到的經驗以及和尼赫魯及其同僚談過幾次話。幸好有一些大使非常同情我們,並且告訴我如何做,所有的大使都答應要轉告他們的政府:我們西藏人請求支援。最後,馬來西亞聯邦以及愛爾蘭共和國支持一項初步提案,這項提案在十月間由聯合國大會辯論,並且以四十五票贊成,九票反對、二十六票棄權而通過。印度是棄權的國家之一。 同樣在我訪問首都的特別行程期間,我會見了許多同情我們的印度政治家,其中包括賈雅.普拉卡希.拿顏(Jaya Prakash Naryan),他真的信守一九五六年時所作的承諾,設立了西藏後援委員會(Tibet Suport Committee)。現在,他覺得有個很好機會說服印度政府,改變對西藏的態度。他的熱誠的確富有感染力,並且深深地打動人,但是我直覺地知道尼赫魯班智達絕對不會改變心意。另一個受歡迎的進展是有消息說:支持世界正義的獨立國際組織---國際法學家委員會,最近發行了一份關於西藏法律地位的報告,完全為我們的立場辯護。這個委員會在年初就受理我們的案子,它現在計劃要舉行一個完整的調查。 在我回到莫梭瑞之後的一個月,我接到一則令人鼓舞的消息,亞非國家會議要在德里召開。這個會議幾乎用全部的時間討論西藏問題。這個會議的會員大部分都曾經受過帝國主義殖民的壓迫。所以他們自然對西藏有好感。他們把現在的我們視為以前尚未獲得獨立的他們。當我收到亞非國家會議全體一致支持西藏的報告時,心中非常喜悅、樂觀,並且開始相信有些正面的事情必定會從中出現。可是,唉!令人十分失望,眼前的情勢明顯的告訴我:尼赫魯首相是正確的。我們西藏人絕對不要以為不久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國家。相反地,我們必須專心致力於建立強有力的流亡社區,當時機最後終於來到時,我們才能返鄉繼續生活,以我們的經驗重建家園。 尼赫魯的土地方案似乎勾繪出上述的希望。在南印度接近米索(Mysore)地區有三千英畝土地,如果我們想要,就立刻可以使用。但是,雖然印度政府這麽慷慨,我一開始有些猶豫要不要接受。我第一次訪問印度時的朝聖之旅期間,就曾經訪問過這個區域,並且知道該區寧靜、人口稀少。但是該地氣候比北印要熱一點,我覺得這些天然條件似乎太嚴酷了。此外,我的行政中心是設在達蘭薩拉,我覺得兩地距離太遠了。 另一方面,綜觀我眼前的處境,我了解必須考慮在印度半永久地居住下來。只有這樣才能開始進行教育計劃、保證西藏文化的延續。最後我得到了結論:我過分重視地理和心理的問題;我感激地接受這片土地。第一批的六百六十六名拓荒者在新年時前往,並著手努力使該區適宜人居。以一英畝一人為基礎,最終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三千人的社區。 一九五九年年底傳來有關兩個組織的消息:由阿.梨庫立帕拉尼所領導的『中央救濟委員會』(CentralRelief Committee)以及『美國西藏難民急難委員會』(American Emergency Committee for Tibetan Refugees )為了幫助我們,已經成立了。稍後也有其他國家成立了類似的服務機構,它們提供了難以估計的援助。 同時,我開始接見一些有趣的人。其中的一位是我在錯模見過的印度和尚,當時他攜帶著一顆佛祖的捨利,雲遊各處。我非常高興能再度見到他。他非常好學,並且對社會經濟學特別有興趣。從上次見面到現在,他花了許多時間和精力要綜合馬克思思想以及佛法。我對他的研究非常感興趣。因為我認為:從泰國邊境一直到西伯利亞,這廣大區域人民的信仰是佛教,現在卻可怕也遭到馬克思主義的宗教迫害,所以這項研究很重要。 同時在這段期間,我也接見了一位左傾的錫蘭和尚。當他快要離開莫梭瑞時,我的新朋友邀請我去斯里蘭卡。斯里蘭卡---這個我非常想去的地方,不只是因為這使我有機會看到佛祖所有捨利中最重要的部分---佛陀的牙齒。然而幾個月之後,即將動身出發之際,我收到一則『難民的地位是這麽不確定』的強力暗示。斯里蘭卡政府發出一則消息惋惜地說,因為不可預見的發展,所以我的斯里蘭卡之行無限期的延後。這些都是北京從中作梗。我再一次被提醒;在高位的兄姊們如果願意,他們甚至應停止宗教活動。 當我接見一個遭中共侵略的東土耳其斯坦受害者代表團時,我面臨與中共展開『有意義的對話』的緊迫需要。東土耳其斯坦在一九四九年被中共佔領。我們彼此間有許多地方可以交談,我們還花了許多時間彼此交換經驗。眾所周知的,東土耳其斯坦的難民比西藏難民多很多,他們的領袖之中,有一位律師。反觀我們,在所有西藏難民中竟然連一個開藥治病的醫生都沒有,更別說是合格的律師了。我們最後討論如何在我們各自的國家內進行爭取自由的抗爭。會談末了,我們同意保持密切接觸,就像我們今天所作的。雖然西藏問題一向比東土耳其斯坦問題更引公眾注意。 十二月時,我又花了六小時旅程下德里,這是我新的朝聖之旅的第一段行程。我想多花點時間停留在一九五七年初我曾經訪問過的地方。旅程中,我再度拜訪尼赫魯首相。我有點急著想知道尼赫魯怎麽說聯合國決議案。我不希望他因此而煩惱。事實上,他熱切地向我道喜。我開始明白,雖然他偶爾表現笨拙,但是基本上他是個非常寬宏大量的人。再一次我又領教到民主的意義。即使我拒絕了他的意見,但是他卻不會因此而改變了對西藏人的態度。結果我比以往更願意聽聽他的話。這和我在中國的經驗恰恰相反。尼赫魯不會滿臉堆著笑容。在他回答之前,他會靜靜地坐著聆聽、顫動的下唇微微凸出,他說話一向坦率、誠實。尤其,他給予我思考的自由。而中國人則是常常面帶著笑容說謊。 我也見到了印度總統拉伽德拉普拉薩德博士。我又再一次成為他宮邸的上賓,作陪的是一位耆那教教徒,他是阿梨圖西(AcharyaTulsi),我非常尊敬他。一九五六年第一次會面時,我就對總統的謙恭留下深刻印象。他的風範超凡,我真得感動得眼淚都流下來了。我把他當成是真正的菩薩。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他住所的花園內。早上我很早就起來散步,發現他也在花園裡,一位長者彎著身,光采奕奕地坐在一張大的黑色輪椅上。 我從德里出發前往菩提伽耶。在那兒,我接見了一個六十人或者更多的西藏難民代表團,他們也正在朝聖。當他們的領袖趨前,並發誓要以生命繼續為西藏自由而抗爭,這真是感人的一刻。之後,有生以來第一次,我為一百六十二位年輕的西藏沙彌受戒,我覺得非常榮幸,這座寺就在佛陀成道的菩提樹旁邊。 接著我旅游到鹿野苑,這是佛陀第一次轉法輪的地方。隨從我的一小群西藏政府官員包括了林仁波切和崔簡仁波切,當然也有服飾、禮節和掌膳總管。我一到達那兒,發現大約有兩千名西藏難民聚集,他們都是新近取道尼泊爾來到印度的,他們知道我計劃在這裡開示。他們的處境都非常不好,但是我可以看到他們是以高尚的心情來面對艱困。西藏人是勤奮的生意人,他們已經擺好了攤子。有些人正在賣那些隨身帶出來的值錢東西,有些人則是在賣舊佈。有許多人只賣茶。我被他們這種面對苦難的力量所激勵。每一個人都可以告訴你他們曾經歷殘暴、 危難的過去,但是他們正在把缺憾的生命所能給予他們的,善加運用。 這個首次、長達一星期的鹿野苑法會對我來說是件奇妙的事。能夠在兩千五百年前佛陀初轉法輪的地方宣揚佛法,意義非比尋常。這段期間,我專注於磨難的正面意義。我提醒每一個人,佛陀曾經說過,『苦』是趨向解脫的第一步。西藏有一句古老格言是這麽說的:衡量快樂的是痛苦(Pain Whatyoumeasure Pleasure by)。 我回到莫梭瑞不久,我知道印度政府計劃把我遷往永久住所----一個叫達蘭薩拉的地方。這是個出人意料而且有些令人驚慌的消息。我在地圖上找到達蘭薩拉,發現它是另一個山站,就像莫梭瑞一樣,但它比莫梭瑞還要荒僻。經過進一步的調查發現,該地不像莫梭瑞,莫梭瑞距離德里只有幾個小時,達蘭薩拉到德里卻要一整天的路途。我開始懷疑印度政府現在是不是打算把我們藏在一個對外連絡不便的地方,好讓我們西藏人從外面世界的眼中消失。 因此我請求是否能允許我派一位官員去達蘭薩拉實地考察,看看這個地方是否合乎我們的需要。我的請求被採納了,我派了一位噶廈的成員——昆德林(JTKundeling)前往達蘭薩拉考察。一星期後他回來說,達蘭薩拉的水比莫梭瑞的牛奶還好。所以我們就立刻準備拔營。 同時,我首次訪問北方各省,以後我也多次訪問北方各省,西藏難民現在正在那裡修築道路。我看到他們的時候,我的心都碎了。兒童、女人和男人都並肩勞作:他們以前是尼師、農夫、和尚,現在都被倉促地編在一起工作。白天,他們必須忍受在大太陽下作整天的重活;晚上,他們擠小帳篷睡覺。還沒有人適應這裡的水土環境,縱然這裡比難民營還涼爽一些,但是濕熱仍然使得我們支付可怕的代價。這裡空氣惡臭、蚊子又多。疾病到處肆虐,這些病常常會要人命,因為這些人的體格早已經陷入衰弱狀態。更糟的是,築路工作本身就非常危險。大部分的道路工程是在險峻的山邊進行,築路時所用的炸藥也會引起意外。 即使到了今天,有一些老人還是帶著當年那種可怕的勞動所造成的痕跡:殘廢、跛足。雖然現在他們的勞動成果已經可以明顯地看到,但當時有些時候看來,這整個冒險的築路工程,是沒有意義的。只要一場猛烈的傾盆大雨就能使他們的努力付諸一片紅泥。雖然他們的處境危險,西藏難民仍然對我個人表示深深的尊敬,並且當我說到撐下去是很重要的時候,他們仔細聆聽。我真的非常感動。 這趟公路營的首次訪問使我知道一項新問題。築路工人的孩子正蒙受了極度營養不良的危機,死亡率非常高。所以我和印度政府接觸,印度政府很快就成立了一個新的、合乎他們需要的營區。同時,第一批五十五位兒童已經被送往莫梭瑞,我們的第一所學校已經在莫梭瑞設立。 一九六○年二月一日,第一批拓荒者抵達米索州的拜拉庫普(Bylakuppe)。我後來聽說,他們看到這一片土地時,許多難民都崩潰並且痛哭。橫在他們眼前的任務是這麽艱鉅。他們只有配發帳篷和基本工具,除了這些之外,他們唯一的資源就是他們自己的決心。 就在一個月之後,三月十日,在我和大約八十名組成流亡政府的官員啟程前往達蘭薩拉之前,我發表西藏人民的抗暴紀念的聲明,以後這也成了傳統。在這第一次的聲明中,我強調西藏人民要以長遠的眼光來看西藏的處境。對我們這些流亡在外的西藏人而言,我說:我們的當務之急是定居下來,延續我們的傳統文化。至於未來,我說出我的信念:以真理、正義和勇氣為武器,我們西藏人終將戰勝,西藏將重獲自由。 |
| © The Office of His Holiness the 14th Dalai Lama. e-mail: service@dalailamaworld.co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