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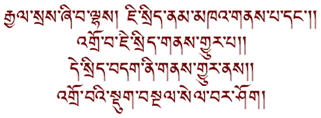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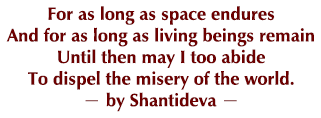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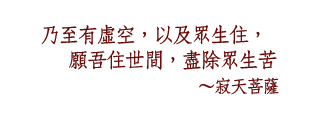 達賴喇嘛格言
若你想得到真正的朋友,首先就必須在周遭創造正面的氛圍,畢竟我們是社會性的動物,而朋友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老是板著臉,對人又充滿不信任,那怎麼可能讓他人心生歡喜、露出笑容呢?這是非常困難的。
相關連結
|
藏曆:2152 木蛇年
⌘ 流亡中的自在 ⌘
第七章:出亡
進入藏境,我坐車進錯模、江孜、日喀則返回拉薩。沿路經過的地方,我都對大眾開示,並邀請西藏與中共官員到場。照例我先作一段簡短的開示,也談世俗之事。我強調藏人有誠實公正的對待中共官方的責任;我堅持任何人看到錯誤都有責任糾正,不論犯錯的是誰;我也要求我的同胞恪守十七點『協議』。我告訴他們那年二月第一個星期我跟尼赫魯及周恩來的談話內容,毛澤東自己曾公開承認西藏尚未作好改革的準備。最後,我提醒他們,中國人宣稱他們來西藏是為了幫助西藏人,如果他們的官員不合作,無異違反共黨政策。我補充道,別人大可以一味歌功頌德,但依照毛主席的訓令,我們該自我檢討才對。在場的中國人對此顯然感到很不安。
我以這種方式向我的同胞保證,我會盡力幫助他們,而且警告新來的外國主人,從現在開始,我們會毫不猶豫的指出一切缺失。但旅程中,我勉強裝出來的樂觀,卻一再受到東部戰況蔓延消息的打擊。終於有一天,政委譚冠三將軍來看我,要求我派一名代表令自由門士放下武器。因為這也是我的心願,所以我欣然同意,派出一名喇嘛跟他們談。但他們並未接受。一九五七年四月一日我到達拉薩時才發現,全西藏的情形不但已不受中共控制,連我也控制不住了。 那年仲夏,從西康直到安多都在作戰。自由門士在岡波扎希的號令之下,人數與日俱增,攻勢也越發凌厲,中共更是奮力還擊,他們不但用飛機轟炸各村鎮,還用砲轟,把整個區域夷為平地。西康與安多居民逃來拉薩,在附近平原搭帳篷居住。他們來的消息有些慘絕人寰,令我覺得難以置信。中共用來嚇阻他們的手段,殘酷得出乎我的想像。直到我一九五九年讀到國際法學家委員會(lnternationai Commission of Jurits)出版的報告,我才算相信了我聽說的這些事:釘十字架、凌遲處死、開堂破肚及分屍都是稀鬆平常。砍頭、火刑、毒打至死、活埋、把人綁在狂奔的馬後拖死、倒吊、或綁住手腳丟入冰水也層出不窮。為防被害者在綁赴刑場途中,大喊『達賴喇嘛萬歲』,還先用掛肉的鉤子扯斷他們的舌頭。 情知大難迫在眉睫,我宣布將在十八個月後,一九五九年的默朗木慶典中接受出家的最後考試,我知道時不我待,我必須盡快結業。同時我迫不及待的盼望已接受我的邀請的尼赫魯早日來西藏訪問(中共大使已欣然批准此事)。我唯願有他在場,中共官方的野蠻行徑會稍見收斂。 這段期間,拉薩的情況與六年前中共初來時相去不遠,不過愈來愈霸道。從這時起,將領們來見我時都全副武裝。雖然他們把槍藏在衣服裡,並不公然佩戴,可是一坐下就原形畢露了。他們還是口口聲聲向我保證原來的那一套,但說多了違心之論,往往使他們滿臉通紅。 此外,預備委員會也還是定期開會,討論一些毫無意義的政策修訂。中共為了粉飾他們企圖在西藏實施的暴政,實在是大費周章。我覺得很無力。但我確信,如果我辭職(我真的考慮這麽做),或正面反抗中共,後果將更加不堪設想。但我也不能不讓拉薩和其他犧牲慘重的地區投降。中共已至少有八個師的兵力在東部;十五萬名訓練精良的人民解放軍,對付牧人和山區居民組成的鳥合之眾。我對將來越想越覺得絕望,似乎不論我們做什麽,都無法改變西藏將成為中共附庸的事實。 我長期居住的諾布林卡宮的生活,也是一成不變。數千尊鍍金佛像在不計其數的長明燈下閃閃發光,提醒我們現世的無常虛幻。每天的例行公事也都照舊,不過我現在提前到五點以前起床,祈禱後獨自做早課,然後我一位親教師會來跟我討論經課的內容,接著我的四名稱廈會來加入,其餘的時間我用於辯論---我的考試就是這種形式。某些特定的日子,我會在宮中多間佛堂中的一間,主持一場供養。 自從中共入侵以來,拉薩改變很大。中共軍官及他們的眷屬形成一個新的區。跡象顯示,有一天現代化中國都市的發展必將吞噬這古都。他們建了醫院、學校---可惜西藏人並未因而受惠---和新的軍營。由於情勢惡化,軍方在他們的營區四周挖築壕溝,堆壘沙袋。他們原來就至少成雙結隊才敢外出,現在更是非大隊人馬才會走出營區。但我跟外界的接觸很少,大部分不幸的消息都是由我的潔役或各級官員帶來的。 一九五八年,我遵照新任達賴喇嘛都必須在寶園中另築新居的傳統,遷入諾布林卡新宮。我的居所跟前輩們一樣,設計得恰容我一個人使用而已,只不過裝潢較現代化,還有幾件電器。我用一張時髦的鐵床取代了陳舊的木箱床;浴室中設有自來水及熱水器,可惜還沒有啟用,我就必須離開諾布林卡了。上下兩層樓都裝了電燈,客廳中陳設著桌椅,而非傳統的西藏座墊,方便外籍訪客;如果我沒記錯,還有一架印度政府贈送的大收音機。這個家完美無缺。屋外有座小池塘,一個漂亮的假山庭園,其中花草都是我親自監督種植的。拉薩什麽都長得好,園中不久就百花繽紛。我在那兒生活很愉快,只可惜為時不久。 西康、安多與西藏中部的戰役不但擴大,初夏已有數万人加入這場爭自由的戰爭,戰事日復一日接近拉薩,雖然他們都很缺乏槍械彈藥。他們的武器有些搶自中共部隊,有些來自一次偷襲西藏政府扎什倫布彈藥庫的斬獲,還有一部分則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所供應。 我流亡期間,雖聽說有關飛機空投武器與金錢的傳聞,但這類行動為西藏人帶來的損害遠超出中共之上。美國人不希望留下援助西藏的把柄,刻意不供應美製的裝備。他們空投的都是粗製濫造的火箭炮及老舊的英制步槍,後者在印度及巴基斯坦都極為普遍,萬一被敵方據獲,也無法追踪來源。它們在空投時往往遭到嚴重損壞,以致無法使用。 我當然不曾目睹過任何一場戰役,但一九七○年代,有位剛由西藏逃出的喇嘛告訴我,他曾經從安多邊遠地帶高山上的隱居山洞中,目擊一場小型沖突。六名騎士攻擊河灣上一人,同時,這些已渡河逃逸的騎士又再次回頭,再度從四面八方側面攻擊,然後才逃入山區。我聽到這種勇敢的事蹟。深受感動。 一九五八年下半,無可避免的危機終於來臨,自由門士聯盟『處溪岡竹』包圍了哲塘一個中共的要塞,距拉薩不過兩天的路程。譚冠三將軍來找我的次數更為頻繁。他外表像個農夫,滿口黃牙,頭髮理得很短,現在他幾乎每週都來,帶著一名神氣活現的通譯,對我勸誘辱罵,無所不用其極。過去他們只一個月來一次。這使我覺得諾布林卡的新會客室令人無法忍受,房裡的氣氛被他們的造訪破壞無遺,我簡直怕進那個房間。 最初,譚將軍要求我動員西藏部隊對付反抗軍。我說這是我的責任,當我指出,這麽一來,士兵可能會陣前倒戈,投向自由門士陣營時,他勃然大怒。此後,他就極力指責西藏人忘恩負義,不會有好下場。最後,他把過錯全推到塔澤仁波切、嘉洛通篤等人(當時均已流亡在外)身上,令我取消他們的西藏公民權。我同意照辦,因為這一些人在國外都很安全,第二我不想激怒中共與拉薩發生正面衝突。我幾乎願意盡一切努力避免這種發展,我相信如果拉薩人捲入戰爭,和平就沒有希望了。 同時,自由門士完全無意妥協。他們甚至希望我認可他們的行動;可惜得是,我年輕的愛國熱情雖然使我渴望能這麽做,但我做不到。我寄望於尼赫魯來訪,但中共於最後一刻取消了訪問。譚冠三將軍宣稱,他們無法保障印度總理的安全,只得撤回邀請。我覺得猶如大難臨頭。 一九五八年夏末,我前往哲蚌寺與色拉寺,接受我最後出家測驗的第一部分考試。我必須跟這兩處學術中心最出色的學者辯論數日之久。在哲蚌寺的第一天,開始時有數千名僧人在大殿中同時誦經,氣氛和諧美好。他們讚美佛陀及諸聖菩薩(大多是印度的聖人與宗師),我聽得泫然欲泣。 離開哲蚌寺前,我照傳統攀登寺後最高峰,俯瞰數百里內風景。此峰極高,連西藏人都有害高山病的危險---但對於在高原上築巢的美麗鳥兒和一種我們稱之為鳥佩的野花卻不嫌太高。這種遍地盛開的花,外形像飛燕草,長得很高而多刺,花呈淡藍色。 但如此的賞心樂事卻因為必須在山區部署西藏士兵保護我而失色不少。在哲蚌寺就有一座中共軍營,四周圍滿鐵刺網和掩體,不時傳出部隊與砲兵練習打靶的聲音。 考驗結束,我回到拉薩才聽說我已以優異的成績通過。一位學問最淵博,名叫佩瑪堅參的方丈告訴我,如果我能有一名普通僧侶那麽多的時間用於研習,成就一定無人能及,所以我很慶幸,我這個學生總算沒有丟自己的臉。 短暫的清靜過後,我發現拉薩的情況更加惡化。因中共迫害前來避難的人數以千計的增加,露宿拉薩市郊,全市人口激增為正常的兩倍;但人心惶惶中,戰事尚未蔓延到此。秋季我去甘丹寺繼續辯論,有的顧問勸我趁此機會去南方『佛法悍衛人士』佔領的地區。初步計劃是我到時應駁斥十七點『協議』,重申我的政府才是西藏合法統治者。我鄭重考慮他們的建議,但我不得不承認,這麽做不會有什麽好處。這種表態只會激怒中共,發動全面攻擊。 因此,寒冷漫長的冬季,我又回到拉薩潛修。次年年初的默朗木期間,我還有一場考試。專心很困難,因為我幾乎每天都聽到中共用殘酷手段對付反抗分子的新報導。偶爾消息對西藏有利----但這不能給我安慰。只有想到我對六百萬西藏人的責任,我才能堅持下去。每天一早,我在房中祈禱,古老的祭壇上諸佛默默在庇佑,我努力培養對眾生的慈悲之心。我再三提醒自己,佛陀教誨要把敵人當作偉大的導師。雖然不易做到,我從未懷疑其中的真理。 新的一年終於來臨,我從諾布林卡宮搬到大昭寺,準備參加默朗木慶典,接著就是最後一場考試。啟程之前,張經武將軍照例來拜年,他說有個新舞蹈團來拉薩,問我有沒有興趣去觀賞。我說有的。他說雖然舞蹈團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表演,但共軍營區的舞台設備較好,最好我能去那兒觀賞。由於諾布林卡確實沒有供表演用的設施,我表示樂意前往。 到了大昭寺,我發現不出所料,聚集在寺廟裡的人比往年都多。除了來自西藏最偏遠地區的俗人,人群中還混有兩萬五千到三萬名和尚。 內廓與外廓每天都濟滿了滿心虔敬循環踱步的信徒。有些人手持法輪,誦念可算是我們國咒的『嗡嘛呢唄美』真言,其他人默默合掌頂禮,五體投地的膜拜。廟前的市場上也濟滿人潮:男女穿著及地長袍,外罩七彩圍裙;得意洋洋的康巴人,用紅繩紮住長辮,來福槍斜掛肩頭;山區來的皺紋滿面的游牧者;孩子們興高彩烈的到處追逐。我從窗中窺視這前所未見的熱鬧場面,今年格外有一股期盼的氣氛,連我這麽避世獨處的人也感覺得出來,似乎每個人都知道,即將有大事發生。 莫朗木的主要儀式(須誦很久的經)一結束,就有兩名中共的下級軍官突如其來的出現,重申張經武將軍請我看舞蹈團的邀約。他們問我什麽時候要去,我答應要等慶典結束,因為我考試在即,暫時沒有空。 考試前一晚,我熱切的禱告,比以前更深切的感到肩上的責任沈重而永無止境。第二天早晨,我要在數千人面前參加一場辯論。上午的主題是因明與認識論,對手是跟我一樣的初級生。下午的論題是中觀與般若,還是跟初級生辯論;傍晚的挑戰不但包括五大部,而且發難者都是年紀遠比我大,經驗也更為豐富的研究生。 到晚上七點鐘,終於一切都結束了。我人已筋疲力盡,但評審團一致承認我有資格獲得學位和佛學研究博士的格西頭銜,卻令我感到輕鬆愉快。 三月五日,我從大昭寺回諾布林卡,照例有光鮮的隨從護駕。這是我們一千多年來未曾間斷的文明最後一次公開展現。我的侍衛穿著色彩鮮豔的禮服,蔟擁在我的轎子四周。後面騎馬跟隨的是滿身綾羅綢緞的噶廈和拉薩的貴族,馬兒都趾高氣揚,彷彿們也知道口中的馬嚼是真金打造。再後面是西藏最有名望的方丈與喇嘛,有的看來仙風道骨、有的卻是油光滿面,像豪商富賈,而不像境界超然的精神導師。 兩地之間長達四英里的道路兩旁,成千上萬的人夾道圍觀,唯一缺席的是中央,這是他們入藏以來的第一次。我的侍衛或軍隊並未因而稍覺鬆懈,軍方派了人在附近的山頭上站崗;表面上是提防自由門士,事實上,他們心目中的敵人完全是另一回事。我的侍衛也有類似的憂慮,他們有些人公開拿勃倫式輕機槍對準共軍司令部,表明了立場。 兩天後,我跟中共官方才又有間接的接觸。他們要確定我去看表演的時間。我選了三月十日。兩天後,亦即表演的前一天,若干中共人員去到我的侍衛總管的家,要帶他去見軍事顧問傳準將,聽取有關我次日到訪應注意的事項。 準將告訴他,中共官方要我們取消一切訪問的儀節,他特別堅持不要西藏士兵隨行,只准兩三名沒有武裝的侍衛陪伴,並且強調他們要求整件事絕對保密。這些要求似乎都很奇怪,我的顧問得知後,討論了很久,但他們還是同意,如果我拒絕前往,一定會引起外交上的重大裂痕及種種不良後果。所以我同意盡量輕裝簡從,只帶數名隨員。 我弟弟天津秋吉也接到邀請。他當時正在哲蚌寺中研究,所以必須獨自前去。同時,命令傳出,第二天通往共軍總部的石橋一帶將實施交通管制。 當然,我的行動要保密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中共這方面的企圖令我的人民大為緊張,因為他們早已在擔心我的安全。消息如野火燎原般散佈開去。 結果是場災難。第二天早晨,我禱告及用餐完畢,趁著晨曦在花園中散佈,突然聽見遠處的吶喊聲。我急忙回到室內,令侍者查明噪聲來源。他們回來告訴我,人群湧出拉薩,向我們這邊而來,他們要來保護我。一整個上午,人愈來愈多,他們有的守住在賓園各個出入口,有人繞牆巡行。中午時已集結了三千人。上午就有三位噶廈差點無法通過前門的人群進來,他們對任何他們認為有私通中共嫌疑的人都懷著敵意。一位由侍衛陪同乘車前來的高級官員,就因被指為叛徒,受了重傷。這真是誤會(一九八○年代,他那位曾參加簽署十七點『協議』代表團的兒子,來到印度,詳細記述了簽約的真相)。後來還真的有人送命。 這消息令我震驚,必須以行動化解這情況,否則憤怒的群眾甚至有可能攻擊中共軍營。人群中很快選出幾位領袖,要求中共把西藏交還西藏人。我禱告上蒼給我鎮靜,同時我知道,不論我個人有什麽感覺,當天晚上我不可能去共軍總部已成定局。我的侍衛總管打電話致歉,並轉達了我盡快重建秩序,說服群眾散去的意願。 但諾布林卡宮門口的群眾堅持不肯離去。他們認為,達賴喇嘛的生命面臨中共的威脅,除非我保證那天晚上不去共軍總部,否則他們絕不離開。我只好令手下官員照他們的意思宣布。但這還不夠,他們又要求我永遠不可走入共軍營區,我再度答應他們後,大部分領袖就回到城內,舉行進一步示威,但諾布林卡有很多人留下。很不幸,他們不了解,留下會比離開構成更大的威脅。 同一天,我派三位地位最高的行政官員去見譚冠三將軍。他們抵達時,發現嘎波嘎旺吉美早已在座。中共人員最初很客氣。但將軍到達時,已掩飾不住心中的怒氣。他和另兩名高級軍官在西藏人面前,痛罵『帝國主義的叛徒』數小時之久,並指責西藏政府秘密組織反對中共官方的動亂行動,甚至還違抗中共的命令,拒不解除拉薩『叛徒』的武裝。共軍將使用激烈手段,粉碎反對勢力。 傍晚,我的代表來諾布林卡的會客室向我報告時,我理解到中共已發出最後通諜。大約六點鐘左右,約七名下級政府官員、留下的人民領袖及若干我的私人侍衛,在賓園外聚會,連署一份駁斥十七點『協議』的宣言,並聲稱西藏不再承認中共的統治。我聽說此事,就通知他們,他們的責任是緩和緊張的情勢,而非使之更形惡化。但是他們對我的勸告充耳不聞。 晚間稍後,譚冠三將軍送來一封信,以溫和得可疑的口吻,勸我為自己的安全起見,遷至他的司令部。他的厚顏無恥令我無法置信。我當然不可能照他的意思行事,但為了爭取時間,我寫了一份友善的回信給他。 次日,也就是三月十一日,群眾領袖向政府宣布,他們要派衛兵在諾布林卡宮外圍的內閣辦公室門口站崗,以防任何行政官員離開。他們擔心一旦若不掌握大權,政府就可能被迫與中共妥協。接著噶廈與這些領袖開會,要求他們取消示威,因為再繼續便有與中共正面衝突的危險。 最初這些領袖們還願意聽從,但後來譚將軍又寫來兩封信,一封給我,一封給噶廈。給我的信與前一封信類似,我還是客氣答覆,承認群眾中有企圖破壞中藏關係的危險分子,我或許該去他的司令部避難(但事實並非如此)。 將軍在另一封信裡,命令官員們要求群眾拆除搭在拉薩城外,通往中國內地的公路上的路障。此舉卻造成反效果。群眾領袖認為,中共要求撤除路障,顯然有增兵以便攻擊達賴喇嘛的企圖,他們斷然拒絕。 我聽說此事後決定該親自跟這些人談談。我向他們解釋,如果人群不自動解散,就面臨被中共部隊以武力驅散的危險。顯然我的懇求多少發生了作用,他們宣布退至布達拉宮山腳下的蕭村,後來那兒曾舉行多次激烈的示威。但諾布林卡宮外大部分人仍然留下來。 大約就在這時,我請示涅衝的神諭。我該留下或脫逃?我該怎麽做?神諭清楚的指出,我該留下繼續與中共對話。我一時之間分不清這是否真的是最好的出路,我想起魯康瓦的話,他說神明走投無路時也會撒謊。因此我花了一個早晨進行另一種降靈儀式『謨』,但結果完全相同。 接下來的幾天在恐懼中含糊度過,我記得接連獲准中共增兵、群眾情緒變得幾乎歇斯底里的報告。我再次請示神諭,但還是如前不變。到了十六日,我接到譚冠三將軍第三封,也就是最後一封信,並附有嘎波的信。譚將軍的信跟前兩封信大致類同,嘎波的信卻肯定了我和其他人的猜測,中共計劃攻擊群眾,並炮轟諾布林卡。他要我在地圖上畫出自己的位置,砲兵就不會轟炸我在的那幾棟建築。真相暴露的這一刻真是太可怕了。不但我的生命有危險,成千上萬的同胞似乎即將喪命----除非我能說服他們解散回家。他們應該知道,他們已向中共展示了強烈的情緒。但這還不夠。他們對這些不受歡迎的外國人所使用的殘暴手段,已憎恨到極點,什麽都不能使他們回頭。他們會死守到最好一刻,為保護他們的『最高保護者』犧牲生命。 我勉強給嘎波和譚將軍寫回信,對拉薩人民中反動分子的可恥行為表示歉意。我向他們保證,我個人認為到共軍司令部避難是個好主意,但揆諸當時的情勢,很難這麽做;我希望他們也能耐心等動亂平息。反正盡一切可能爭取時間!畢竟群眾不可能一直耗下去。我故意不告訴他們我的住處位置,希望籍此再拖延一陣子。 把信送出後,我真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麽辦。第二天,我再度請示神諭。令我大吃一驚,神指示:『快走!快走!今晚! 』處於慌惚狀態的靈媒蹣跚地向前,抓起紙筆,相當清楚而明白的繪出我該循什麽樣的路線離開諾布林卡宮,直奔印藏邊界。他的指示跟一般預期不盡相同。神諭結束後,擔任靈媒的名叫羅桑吉美的年輕和尚頹然倒地,代表金剛扎滇已離開他的身體。就在這時,彷彿要強調神諭的威力似的,兩枚砲彈在賓園北們外的沼澤中爆炸開來。 回顧三十一年來的往事,我確信金剛扎滇已知道我必須在十七日離開拉薩,但他怕洩露天機,一直不肯明講。沒有計劃就不會走漏消息。 但我並沒有立刻準備逃亡。我首先要確定神諭正確無誤,因此我又作了一次謨,結果與神諭完全符合,但突破封鎖的機會非常小。不但守在門外的群眾對所有進出的人都要先搜身查詢一番,嘎波的信也說得很清楚,中共已考慮到我可能企圖逃走,他們一定會防範。可是神意卻與我自己的推理相同:我相信只有我離開,人群才會散去;我不在宮內,他們也就沒有理由留下。因此我決定服從神的旨意。 情況危急,知道我決定的人數愈少愈好,所以我一開始只通知了我的侍衛總管和去結堪布,由他們負責準備一行人當晚出宮的事宜,但同行究竟有那些人,誰也不知道我們一邊討論逃亡的方法,一邊決定逃亡的成員。我只帶最親近的顧問,包括我的兩位親教師,以及當時與我同住的家人。 那天下午,我的親教師和四位噶廈躲在板車後面的帆布罩下混出宮去;傍晚,我母親、我弟弟天津秋結和姐姐澤仁多瑪經過化妝改扮,以前往奇處河兩岸的尼庵為籍口出宮。接著我召見群眾領袖,把我的計劃告訴他們,強調我不但需要最充分合作(這一點我早有把握),也需要絕對保密。我確信中共會在群眾中派出密探。這些領袖走後,我寫了一封信轉達給每一個人。這封信會在次日送達他們手中。 天黑以後,我最後一次來到專門供奉大黑天的佛壇前,他是我的護法。我推開沈重而吱吱作響的門,走進室內,頓了一下,把一切景像印入腦海。許多和尚在護法的巨大雕像基部誦經禱告。室內沒有電燈,數十盞許願油燈排列在金銀盤中,放出光明。壁上繪滿壁畫,一小份糌粑祭品放在祭壇上的盤子裡。一名半張面孔藏在陰影裡的侍者,正從大甕裡舀出牛油,添加到許願燈上。雖然他們知道我進來,卻沒有人抬頭。我右邊有位和尚拿起銅鈸,另一名則以號角就唇,吹出一個悠長哀傷的音符。鈸響,兩鈸合攏震動不已,它的聲音令人心靜。 我走上前,獻一條白絲的哈達。這是西藏傳統告辭儀式的一部分,代表贖罪以及回來的意願。我默禱了一會兒,和尚們一定猜到我要走了,但他們必然會替我保密的。離開佛壇前,我坐下讀了幾分鐘佛經,對一個談到『建立信心與勇氣』之必要性的章節沈吟良久。 我退出時,令人熄滅建築物中其他各處的燈火方才下樓,看見我的一頭狗。我拍拍它,幸好跟我並非特別親近,分離不太困難。我對於不得不留下我的侍衛潔役之事,難過得多。隨後,我步入室外寒冷的三月空氣中,建築物正門外有片平台,而側有樓梯下到地面。我在平台上走了一圈,佇立遙想平安抵達印度的情景。回到門口,我又重思將來重回西藏會是什麽情形。 十點差幾分,我換妥了不熟悉的長褲和一件黑色的長大衣,右肩扛著一支步槍,第二任達賴喇嘛遺下的唐卡,捲成一長卷,扛在左肩。我把眼鏡收進口袋,心中十分害怕。兩名士兵陪著我,他們默默的送我到內院門口,我的侍衛總管在那兒接應。我跟著他們,在一片黑暗中摸索出了花園,到達外院門口,去結堪布等在那兒,我只模糊看見他的人影,佩戴一把劍。他低聲要我一直跟在他身旁。走出大門時,他大膽的向聚集在門外的人宣布,他正在作例行的巡視,我們獲准通過,沒有人再說話。 我蹣跚走過,覺得四周都是人,但他們沒有註意我們,幾分鐘後,我們就順利的出了人群,下一步是如何通過共軍的關卡。被俘的念頭令我很害怕。我有生一來第一次真正覺得怕---倒不是為我自己,而為數以百萬計把信心寄託在我身上的人民。如果我被捕,一切就都完了。我們也有被不知情的自由門士誤會為中共士兵的可能。 我們的第一重障礙是奇處河的支流,我小時常來這兒,直到塔湯仁波切禁止這麽做為止。渡河靠踏腳石,不戴眼鏡非常不好走,我好幾次差點跌倒。渡河後,我們直奔奇處河岸,抵達之前,遇見一大群人,侍衛總管跟他們的領袖簡短的談了幾句,我們才上到河岸。幾重難關正等著我們和擺渡的幾名船夫。 雖然每一揮漿,我們都擔心會引來一陣機關槍掃射,但渡河過程很順利。當時拉薩駐有數万人民解放軍,他們不可能不在四處巡邏。河對岸有一隊自由門士,牽著小馬在等著我們。我在這兒跟我母親、弟弟、姊妹和親教師會合。我們一塊爾等尾隨的幾名高級官員趕到。等待的當爾,我們低聲的批評了幾句中共把我們逼上這條路的惡毒行徑。我也戴回眼鏡---我不能再忍受什麽都看不見的生活---但一戴上我就後悔了,因為這麽一來,我就看見距我們數百碼外,中共軍營中的衛兵所持的火把。還好有云遮住了月光。 其他人到齊,我們就趕往劃分拉薩山谷與昌波山谷的切拉山隘。清晨三點鐘左右,我們在一座簡陋的農舍休息,以後數週,我們經常在這樣的地方尋得庇護。我們不敢久留,略事休息就繼續趕路,八點左右到了隘口。我們趕到前不久天才亮,我們才看出此行是何等倉促。為我們備馬的寺院一方面沒有心理準備,一方面也因為天黑,結果最好的馬配上最差的鞍轡,騎的人也不相稱;反而最老最醜的騾子配著最光鮮的鞍具,背負地位最高的官員。看來十分可笑。 海拔一萬六千尺的切拉隘口(CheLa為多沙的隘口),替我牽馬的馬夫停下腳步,調轉馬頭,告訴我這是一路上最後一次看見拉薩的機會。山腳下的古城顯得平靜莊嚴,一如往昔。我禱告了幾分鐘才下馬,走上多沙的山坡,我們又休息了一會兒才再度向昌波河出發。中午前我們到達河岸,這兒只有一處可以擺渡,我們唯願人民解放軍沒有搶先趕到。他們果然沒有 。 河對岸,我們在一座小村停留,居民很多人都流著淚來迎接我們。我們現在處於西藏最邊遠地區的邊緣,只有稀稀落落一兩處村落,自由門士已佔領了這一帶。從這裡開始,我們周圍便有成千上百不現身的游擊隊戰士,他們已經知道我們要來,而且會一路保護我們。 中共追補我們並非易事,但如果他們得知我們的行踪,或許能預卜我們的路線,派兵攔截我們。因此除了安排三百五十名西藏士兵沿途保護我們,還有五十名左右的游擊隊,而逃亡隊伍本身也擴大到將近一百人。 幾乎除了我以外,每個人都是全副武裝,甚至我私人的廚子也扛著一具火箭炮,腰間掛滿了砲彈。他是個曾受中央情報局訓練的年輕人,迫不及待的想一試他那外表嚇人的偉大武器。有次他還真的伏在地上,發射數枚砲彈,聲稱他已發現了敵人陣地。但重裝彈藥太花時間,我確信他碰到真正的敵人一定會措手不及。整個而言,這場表演並不出色。 我們隊伍中還有一名中央情報局特工,他會操作無線電,而且顯然一路都跟他的上級保持聯絡。他到底聯絡的是誰,我到現在都還不知道。我只知道他隨身攜帶一台摩斯發報機。 當天晚上,我們住在惹美寺,我在此草草寫了一封信給班禪喇嘛,告訴他我已逃走,勸他可能的話來印度跟我們會合。自從仲冬收到他的新年祝賀以來,我一直沒有他的消息。他在另一封秘密信中提到,國內情形整個惡化,我們該籌謀未來的對策。這是他第一次不受中共箝制的表現。遺憾的是我給他的信都未能送到他手中,他也一直留在西藏。 下一個隘口名叫沙波拉,我們於兩三天後走到。山頂上極冷,而且正下著一場暴風雪。我開始為若干同伴擔心。我自己年輕力壯,但隨行的一部分老年人已難經旅途勞苦。由於還未脫離被中共攔截的重大危險,我們也不敢放慢腳步,尤其中共在江孜與空波的駐軍隨時可能包抄,把我們手到擒來。 我起初打算在距印度邊界不遠的隆次宗暫作停頓,在此駁斥十七點『協議』,宣布恢復我的政府為西藏合法政府。但第五天,一隊騎士趕來報告一個可怕的消息,我們出亡四十八小時後,中共開始炮轟諾布林卡,用機槍掃射尚未離開,手無寸鐵的群眾。我最壞的預感都已實現。我知道,跟如此殘酷不仁的人談判是沒有用的,我們唯有走得越遠越好,而趕到印度還有好幾天的旅程,中間還有重重高山阻隔。 一個多星期後,我們終於來到隆次宗,停留了兩天,剛好夠我駁斥十七點『協議』,並宣布成立政府,是為西藏唯一合法的統治機構。約有一千人參加就職儀式,我希望能多停留幾天,但消息傳來,中共部隊已逼近,我們只有往印度邊界撤退,直線距離只有六十英里,但實際行程則大約兩倍遠。中間還需要翻越一座高山,得走上好幾天,我們的馬匹已相當疲倦,草料不足, 們必須經常休息,以恢復體力。啟程之前,我派一小隊體能最佳的人先行,盡快趕到印度,就近讓那邊的官員知道我計劃請求政治庇護之事。 我們由隆次宗來到名叫爵惹的小村,然後趕往卡波山隘,這是通過邊界前最後一座隘口,即將爬到山頂時,我們蒙受一個嚴重的打擊----忽然出現一架飛機,直接由我們頭頂飛過。它過去得太快,以致沒有人看清機身上的標誌,但機上的人一定看見我們了。這不是好兆頭,如果它是中共的飛機,而且非常可能是,他們就知道我們現在的位置了。如此,他們就可以從空中攻擊我們,我們完全無法保護自己。無論這架飛機來自何處,它都強烈的提醒我,我在西藏任何地方都不安全。我對自己出亡的一切遲疑與猶豫都因這項認識一掃而空;印度是我們唯一的希望。 不久之前,我派往印度的先行隊伍回來報告,印度政府已表示願意收留我。聽到這消息,我鬆了一口氣,因為我不願未得允許踏上印度的土地。我在西藏的最後一夜,住在一個名叫芒茫的小村。一到這個雪國的最後前哨站,就開始下雨。一周來天氣都極為惡劣,我們一路在暴雪中掙扎前進,大家都筋疲力盡,實在不需要雨水,但傾盆大雨一夜不停,更糟的是我的帳篷漏水,不論我怎麽挪移,都避不開如注湧入的雨水,我前幾天已經在發燒,這麽一來更惡化成為嚴重的痢疾。 第二天早晨,我病得無法行動,全隊只好留下。同伴把我搬到鄰近的小屋裡,但它所能提供的庇護並不比我的帳篷高明,而且地面上冒出的牛羊臊氣令我無法忍受。那天,我聽見我們攜帶的手提收音機報導,我正在前赴印度途中,但我因跌下馬背,受了重傷。這使我略為開心一點,因為我至少躲過了那樣的災難,但我知道我的朋友都會很擔心。 第二天,我決定繼續上路。跟一路護送我們從拉薩來此的士兵和自由門士道別,又是一件困難的工作,他們現在得回去面對中共。有一名我的官員決定留下,他說他知道在印度發揮不了什麽作用,不如留下來作戰。我實在欽佩他的決心和勇氣。跟這些人含淚作別後,有人幫忙我躺在母犏(dzomo)背上,因為我還是病得無法騎馬。我就以這麽尷尬的姿勢,離開了祖國。 |
| © The Office of His Holiness the 14th Dalai Lama. e-mail: service@dalailamaworld.co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