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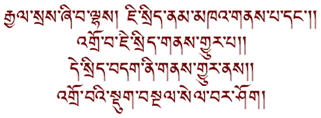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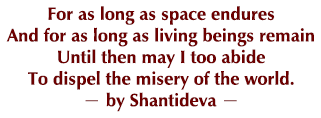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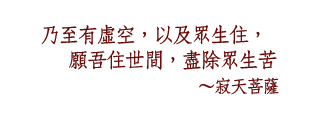 達賴喇嘛格言
我想,假如地球上不再有任何人類,那麼地球本身將變得更安全,世上數以百萬的魚類、雞隻和其他小動物,都更可能享有某種真正的自由。
相關連結
|
藏曆:2152 木蛇年
⌘ 流亡中的自在 ⌘
第六章:尼赫魯懊悔了
一九五五年六月,我返回拉薩,如同以往,受到數万民眾的歡迎。我長期出去在外,藏人非常憂愁,如今我又回來了,這使他們的心為之一鬆;我的心也一樣。顯然,中共在這兒的所做所為要比在東藏收斂多了。返鄉的路上,我受到許多百姓、部落酋長代表團的請求,他們請我懇求中共改變對鄉村地區的政策。他們看到中國人直接威脅到西藏生活方式的作法,覺得非常害怕。
在城裡,我發現情況相對地正常些,不過現在許許多多的卡車、汽車帶來噪音和污染;這是拉薩有史以來第一次。糧荒也紓解了,交織著怨恨的消極抵抗,已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爆發的憤怒。現在我回來了,社會上甚至再度出現樂觀的氣氛。從我這方面來說,我覺得我在中共西藏地方當局的地位,必須靠毛公開對我表示信任才能增強;我也審慎地對未來抱著樂觀看法。 我察覺到外面的世界已經背棄我們了。更糟的是,印度---我們最近的鄰國、精神上的顧問,已經默認北京對西藏所作的聲明。一九五四年四月,尼赫魯簽署了一項新的中印條約---內容包括了班察希爾備忘錄,備忘錄中同意中印雙方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干涉對方的內政。根據這項條約,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 中共當局與西藏行政當局,歷經十年的緊張共存後,一九五五年的夏天無疑是最好的一段共處時光。但是西藏的夏季太短了,沒有多少個星期,中共在西康、安多的活動就傳進我耳裡。中共不但沒有讓藏人過自己的生活,反而開始片面地強制推行各種改革。中共針對馬匹、土地和牛群徵收新稅,破壞之餘還外加羞辱,連廟產也要清算、扣稅,許多財產被沒收充公,中共地方乾部也依據他們自己的政治意識形態來重新分配土地。地主被公審,並且以『反人民』的罪名受到懲罰,令我恐怖的是,有些甚至被處死。中共當局開始把這些肥沃區域游牧耕作的數万農夫集中起來。對我們的新主人來說;『游牧生活』令人厭惡,因為它帶有野蠻的意味(事實上,中國人叫西藏人『蠻子』)。 寺廟的事務橫遭中共干涉,中共也開始灌輸地方民眾反宗教的觀念。和尚和尼師都蒙受極大苦惱,他們遭公開羞辱,強制參加消滅昆蟲、老鼠、鳥以及所有害獸、害蟲的計劃,中共當局明明知道殺生違背佛陀的教義。如果他們拒絕,中共就施以毒打。與此同時,中共在拉薩卻依然若無其事。中共不干涉首邑的宗教活動,顯然希望他們在別處為所欲為時,還能留給我一個安全的假象。 一九五五年年底時,西藏自治區預備委員會的成立大會開始籌備,毛澤東打算以軍事代表團來統治。但是秋去冬來,從東藏傳來更壞的消息。不習慣外來干擾的康巴人,對中共的方式並未溫順以對:在康巴人的財產中,他們最重視的就是自己的武器。所以地方乾部一開始沒收武器時,康巴人就激烈地反抗。整個冬季裡,形勢迅速惡化。逃避中共壓迫的難民開始逃到拉薩,並傳出野蠻、墮落的恐怖遭遇。中共以邪惡的方式鎮壓康巴人抗暴:他們不僅公開毒打、處死抗暴分子,並且往往強迫受害者的親生兒女來執行。公開的自我批判也被引進,中共尤其喜歡這個方法。中共用繩索把犯人縛綁得雙肩脫臼,當這個人完全無助,並且痛苦地哀號時,群眾----包括女人和小孩,都被中乾驅迫痛打那個人。顯然中共認為這種方法能改變人民的心,並且有助於政治再教育的過程。 一九五六年年初,在羅薩節期間,我和涅衝神諭有一次非常有趣的會面。涅衝神諭說,摩尼寶光(這是藏人所熟知的達賴喇嘛名號之一)將照耀西方。我以為這句話是指示我將會在那一年赴印度旅遊。我現在才明白這個預言有更深的含意。 更令人關切的事是許多從西康、安多逃出來的難民最近已經到達拉薩了。整個城市在沸騰。這是首次帶有政治意味的新年慶典。全城貼滿了指責中國人的告示,到處在散發傳單。民眾舉行公開聚會、推選領袖。以前西藏從未發生過這種事。自然地,中國人非常生氣。他們迅速逮捕了三個人。他們說,這三個人應對煽動反民主的罪行負責。但這並不能減少藏人公開反抗中共的統治。 在默朗木法會期間,安多和西康的商業領袖開始募款,為下半年舉行的色翠千嫫儀式作準備。這項儀式是供養西藏的守護神、懇求他們賜予達賴喇嘛長壽、成功。募款活動進行得非常成功,他們獻給我一個非常大、滿佈珍貴的黃金寶座。然而,我後來發現,這項活動有別的目的。它也標示『處溪岡竹』聯盟的形成。 『處溪岡竹』的意思是四河、六山——這是西康和安多兩省的傳統簡稱。這個組織後來協調指揮廣大的游擊抗暴運動。 在默朗木法會後,西藏自治區準備委員會開幕儀式的籌備工作仍繼續進行;我個人是該委員會的主席。幾個月內,中共驅迫藏人建築了三棟龐大的公眾建築物:供前來西藏訪問的中共官員居住的賓館、一間澡堂以及市政廳。市政廳是一棟現代化、有波浪狀鐵屋頂的兩層樓建築,能容納一千二百人,前面是一個高起的平台;另外上面有一個廊台可以坐三百人。這棟建築物正好就蓋在布達拉宮前面。 一九五六年四月,當時中共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元帥偕妻及一個代表毛主席的龐大代表團從北京來到拉薩。我記得訪問中國時,曾見過陳毅元帥。私底下他是個非常好的人,但是他扮演說者角色的風評卻令人畏懼。他曾經作過一場整整七小時的演說。這群中共官員都打著領帶,其中,陳毅神采傲然,雖然他似乎不知道該怎麽打領帶。他的襯衫剛好包住 他的肚子。但是這些都沒有困擾他:他是快活的人,喜歡奢華、滿有自信。他的到來象徵了一場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開幕了。中國人豪華的招待陳毅元帥,為了對他表示敬意,中共地方乾部舉行多場宴會和演講。西藏自治區預備委員會的開幕儀式正式在市政廳舉行時,市政廳裡到處都是旗子和毛主席、 中共主要人物的照片。中共軍樂隊演奏,黨歌飄蕩。真是熱鬧非常。陳毅元帥作了一場(比較短)演講,他聲稱『必要的改革』將引進西藏,以『去除』 西藏的落後情況,他解釋此舉是為了要把西藏提升為『進步』的中國國民的地位,因此這些改革是必須的。接著是中國人和西藏人上台阿諛奉承,他們一致讚揚社會主義和共產黨,並且歡迎中共來西藏。我甚至也親自說了一些,還直率的補充說,我確信中國人會信守承諾、依照人民所希望的步調引進改革,並且准許信仰自由。 西藏自治區預備委員會的組織包括了經濟、教育、農業、電訊、醫藥、 宗教和安全等部門。大部分都由藏人主持。昌都的行政也畫歸拉薩。如此組成了所謂的西藏自治區。然而,西康的其他部分以及安多全境卻由北京直接控制。委員會本身是由五十一位地方代表組成。只有五位是中國人。同時,噶廈和國會都被保留,雖然事實很明顯,中共想要使其邊際化,最後清除一切傳統政府的痕跡。雖然在表面上西藏自治區預備委員會標示著邁向自治的重大進展,但實際上卻不是這麽回事。當陳毅宣布任命時,這五十一位代表(沒有一位是選舉產生)證實全部是中共的應聲蟲:只要不說反對中共的話,他們就可以保有權力和財產。換言之,這是一場丑劇。 儘管如此,還有一些令人驚奇的事。其中之一是羅桑桑天被指派為新近成立的安全部門的一員。他是個非常仁慈、溫和的人,沒有人比他更適合擔任這個職位。我永遠忘不了他和中共同僚開完會後,他臉上的表情,一切進行得還不錯,直到有個人朝著羅桑桑天(他會說一點中國話)問道:【『殺他】的西藏話怎麽說? 』在這之前,我的哥哥曾認為這件新差事相當令人高興,並且是份正直的工作,但是這個問題使他驚惶失色。他心中甚至沒有殺一隻昆蟲的想法,他忘了這些字。當天傍晚他來諾布林卡時,臉上充滿了慌亂。 『我該怎麽辦? 』他問道。這個故事是中國人與西藏人態度差異的另一個說明。對中國人來說,殺人是生命的事實;而對西藏人而言,這實在無法想像。 西藏自治區預備委員會成立後不久,我聽說西康的中共地方當局試圖說服所有地方的領袖。中共把他們都召來,要他們投票表決引進民主改革,尤其是意指設立幾千個集體農場,這些農場包括噶處、卡色地區的一萬個家計單位。在這三百五十位地方領袖中,在我和內閣同意接受時,大約有二百名同意進行改革。四十位說他們準備立刻接受改革。其他的人則說他們永遠不要這些所謂的改革。會議之後,中共就放他們回去了。 一個月之後,那些持反對意見的人又被中共召集了,這一次是在昌都東北邊一個叫爵姆達宗的堡壘開會,他們一進入堡壘,堡壘就被五千名軍隊團團包圍,中共告訴這群俘虜,除非他們同意接受改革,並且答應協助進行改革,否則就別想走。關了兩個星期後,這群康巴人放棄了。他們似乎別無選擇。然而,那天晚上,看守堡壘的士兵減少了。看到了這個機會,每個康巴人都趁機逃走,上山去也。一下子,中共製造了一個反對的中心,在往後的許多年裡,給中共帶來很多麻煩。 大約在我接到一份報紙的同時,發生了爵姆達宗事件。這份報紙是由西康卡色的中共當局所發行。我不敢相信我看到的是一列被斬斷的人頭。照片標題說這些頭是反革命罪犯的。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共暴行的具體證明。因此,我知道我所聽到的每一件關於我們新主人所干的可怕事情,是真實不虛。中國人也發覺這份報紙對人民產生的反效果,於是就試著收回---甚至還花錢收購。 由於這件新資訊,使我連帶了解西藏自治區預備委員會不過是『洗眼水』。我開始懷疑未來是否還有什麽希望。我先世所作的預言現在已經證明是完全正確的。我覺得厭煩。表面上,我照舊過日子,祈禱、靜坐,並且在親教師的指導下,努力研讀。我也和以往一樣參加所有的慶典、儀式,時常接受開示。有時候,我運用職權離開拉薩出外旅遊、訪問各個寺廟。有一次我到瑞廷寺---前任攝政的法座,它在拉薩北方,要走好幾天。啟程之前,我收到一封信,這封信是一位已經流亡在外的西藏要人所寫的。但是拉薩的現況是如此陰沈,我甚至開始起疑,所以我沒把信拆封,隨身收藏,到了晚上才小心地把它放在枕頭下,直到我前往瑞廷寺。 能離開拉薩,遠離一邊努力和中共當局共事,同時一邊冀能限制他們造成傷害的憤怒,真是一種解脫。如同以往,我盡量簡單,並且微服出遊。這樣我才能見到當地人民,聽聽他們怎麽說。在一個特別的場合裡,在距離瑞廷寺不遠的地方,我和一位牧人閒聊。 『你是誰? 』他問道。他長得又高又壯。頭髮既長且粗,就像犁牛一般。 『我是達賴喇嘛的僕人。 』我回答道。我們談到他在鄉間的生活,他對未來的希望、害怕。他過渡忙於在這片貧瘠的土地上討生活,以致無法顧及城里以及城外的現況。 可是因為他非常純樸,我很高興發現他的宗教信仰深厚;即使在這偏遠的地區,佛法也如此興盛。他過著普通的農民生活,適應自然和環境;但是對他眼前地平線以外的世界卻不太有興趣。我詢問他和地方政府官員打交道的經驗如何。他告訴我,多半都公正,但是有一些官員好管閒事。對這次談話,我非常高興;因為這給我許多有用的見識。尤其我還學到:雖然這個人完全沒有受過教育,但是他知足;雖然他沒有最起碼的物質舒適,但是他安全、無慮,因為他所過的生活就像以往無數代祖先所過的一般,無疑地,他的孩子、孫子也會同樣生活下去。同時,我了解到這種世界觀已經不合適了,不管共產黨搞得怎樣,西藏人無法再活在刻意選擇的寧靜隔絕中。最後我們告別時,成了最好的朋友。 但這故事還沒完。第二天,有人請我對下一個村落的人說法、加持,這個村落就在我們的旅途上。他們為我準備了一張暫時代用的法座,有數百人前往與會。剛開始進行得還不錯,但是當我觀望四周時,我看到那位朋友就站在人群中,他的臉上帶著一種令人憐憫的迷惑。他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對他微笑,但是他只是傻傻地看著我。我覺得相當抱歉,因為我昨天欺騙了他。 等到我確實來到瑞廷寺時,我在該寺最重要的佛像前禮拜,我記得當時也沒有什麽特別的理由,我的心情卻非常激動。我強烈地覺得我和這個地方有甚深的因緣, 從那時開始,我就常常想到要在瑞廷寺蓋一間茅篷,安度餘年。 一九五六年夏季,發生一件事,幾乎使我淪入此生中鬱鬱寡歡的一段時光。康巴和安多的自由門士聯盟開始贏得了可觀的戰跡,在五六月時,破壞中國軍事公路的許多路段、炸毀許多橋樑。結果使得人民解放軍徵調四萬大軍增援。這就是我所害怕的事情。不管抗暴多麽成功,中共最後會以龐大的兵力、優越的火力擊敗反抗軍。但是我沒能預知中共會空炸西康理塘寺。我得知此事後,痛哭了一場,我無法相信人類會如此殘忍。 轟炸之後,接著是殘酷的拷問、處決婦女和兒童----這些人的父親和丈夫加入抗暴運動。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中共也謾罵僧尼。在拘禁之後,中共強迫這些單純的宗教人士公開地彼此行淫,甚至強迫他們殺人。我不知道該作些什麽,但是我作了一些我必須要做的事。我立刻要求會晤張國華將軍。我告訴他,我想寫信給毛主席。 『如果你們這樣倒行逆施,西藏人怎能夠信賴中國人? 』我詢問道。我直率地告訴他,他們這樣作是錯的。但是這樣一來反而引起一場爭執。他說我的批評是污衊祖國----我只是想保護、幫助我的子民啊!如果我的同胞有人不想要改革---改革將會澤及群眾,因為改革可杜絕剝削---那麽他們就會受懲罰。他的理由真是非常瘋狂。我告訴他,這並不能證明殘害無辜的人是合理的,尤其還從空中丟炸彈轟炸他們。這次會晤當然沒有什麽效果。張將軍堅持他的立場。我只有寄望毛主席能看到他的部下陽奉陰違的行動。 我迳自寄了一封信。但是沒有回音。所以我又透過官方管道寄了另一封信。同時,我也勸撲錯汪結親自呈送第三封信給毛主席。但是也沒有收到回信。一個星期又一個星期過去了,我仍然沒有聽到北京的回音。我開始首次真的懷疑中共領導人物的意圖,這件事使我震驚。在訪問中國之後,雖然我曾經有許多負面的印象,但是在基本上,我對共產黨還是持肯定的態度。然而,現在我開始把毛主席的話看成是彩虹美麗,但沒有實質。 撲錯汪結在西藏自治區預備委員會成立時,抵達拉薩。再次見到他,我非常高興。他仍然像以前一樣信奉共產主義。在四月的慶典之後,他陪同某些中共要員去視察邊遠地區。回來之後,他告訴我一個好笑的故事。中共的一位高級官員問一位住在邊遠農村的農民說:『你對新制度的看法如何? 』這個人回答說他相當快樂,除了一件事----新稅。 『什麽新稅? 』官員追問道。 『拍手稅。每一次有中國人來訪問,我們都必須出去、拍手。 』 我一向以為只要毛主席繼續信任撲錯汪結,那麽西藏就有希望。在他回去北京後,我向張國華將軍提出一項要求:請派撲錯汪結為黨書記。起初是原則上同意,但是有好久都沒有下文。 一九五七年年底,一位中共官員通知我:撲錯汪結不會回西藏了,因為他是個危險分子。聽到這個消息,我很驚訝,因為毛主席很器重他。這位官員解釋說,有許多理由,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撲錯汪結還在西康,未去拉薩之前,組織了一個不讓中國人加入的西藏共產黨。因為這項罪名,所以他被降級、不准回西藏。聽到這個消息,我感到難過---第二年,我得知我的老朋友被革職、拘留時,我更是覺得難過。最後,他被關進監牢。被定為『非人』,一直做牢,直到七○年代的晚期。每個人都知道他是個真實、奉獻的共產黨員,但是仍不免遭此劫難。這件事使我知道中共領導人物不是真的馬克思主義者---奉獻自己,造福大眾,使世界更好。他們事實上只是一群極端的國家主義者。他們只是扮演成共產主義者的大漢沙文主義者:一群心胸狹窄的狂熱分子。 撲錯汪結現在仍然健在,但是垂垂老矣。在他死之前,我非常想再見他一面,我仍然非常尊敬他,因為他是一位元老的、有經驗的西藏共產黨員。現在的中共當局明白這一點,我仍然有希望能再看到他。 一九五六年春天,拉薩來了一位非常受歡迎的貴賓---錫金的摩訶羅庫瑪(Maharaj Kummar,皇太子)。錫金就在藏印邊界上,距離錯模不遠。他是個可愛的人:高大、寧靜、溫和、鎮定,耳朵很大。他帶來一則好消息----一封由印度摩訶菩提學會發出的信,他本人是該學會的會長。這個組織----代表這個次大陸上所有的佛教徒,邀請我去參加佛陀二千五百年誕辰紀念。 我非常高興,因為對我們西藏人來說,印度是聖地。我一直渴望能去印度朝聖:印度是我最想訪問的地方。此外這次遠行印度,我也許有機會和班智達尼赫魯以及聖雄甘地的其他繼承人會談。我實在很希望能和印度政府聯絡上;如果我能看到民主是怎麽運作就好了!當然中共有可能不讓我走,但是我總得試一試。所以我拿了這封信去找范明將軍。 不幸的是。范明是一個非常惹人厭的中共地方官員。他很有禮貌的接待我。但是當我說明赴印度訪問的理由時,他就打起太極拳。他認為這不是個好主意。印度有許多反革命分子,它是個危險的地方,此外,現在預備委員會事情很多,他懷疑我是否有空。 『不管怎樣,』他說:『這只是個宗教性學會的邀請,並不是印度政府邀請您。所以不要擔心,你不必非要接受不可。 』毀了!事實擺在眼前,中共當局甚至想妨礙我履行宗教上的義務。 幾個月過去了,這段期間沒有再提起佛陀誕辰的事。接著在十月中旬的某一天,范明和我聯絡,詢問我要提名誰當代表團團長:印度方面想知道。我回答說:我想派我的初級親教師崔簡仁波切;我補充說,只要他一批准,這個代表團就可以準備起程。又過了兩個星期,我漸漸地把這件事淡忘了;突然,剛從北京回來的張經武將軍前來告訴我,中國政府決定還是讓我去好了。我簡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我太高興了。 『但是小心點! 』他警告我。 『印度有許多反革命分子和間諜。如果你敢跟他們玩什麽花樣,我希望你知道,在匈牙利、波瀾發生的事,就會在西藏重演。 』(他是指蘇聯血腥鎮壓這兩個國家的抗暴運動。)當他說完這些話時,我知道我應該隱藏我的狂喜,並且應該裝出一副非常憂慮的樣子。我表示,我確實很驚訝,並且擔心他所提到的帝國主義者和反革命分子。這些話使張將軍放心了,他改用一種安慰的口吻對我說:『不要擔心太多。 』他說:『如果你有任何困難,我們駐印度大使館幫助你。 』我們的會談到此結束。張將軍站起來,行完禮之後,就離開了。他一出門,我就忍不住爆笑,好像嘴巴都笑開咧到耳根了,我急忙把這件消息告訴我的侍者。 在我們啟程前的一些日子裡,我聽到一個有關中共當局如何突然改變態度的趣事。據說印度駐拉薩的領事曾詢問我的官員,我是不是真的能去印度參加佛陀誕辰慶祝會?他們回答說『不行』。這位領事就把這件事告訴印度政府---結果尼赫魯就出面為我說項。但是中共當局仍然不願意讓我去。直到張將軍回到拉薩,發現那個印度領事已經把尼赫魯說項的事情告訴許多人,為了怕損傷中印關係,中共被迫改變心意。 將近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底,我終於得以離開拉薩。我充滿喜悅,一心盼望能自由行動,不再受到某些中共官員或其他人的嚴密監視。 我的隨員很少,感謝四通八達的軍車公路連通中國和西藏,我們現在能一路坐車到錫金。在日喀則,我們停下來接班禪喇嘛,然後繼續開往春比塘(Chumbithang)---這是那突隘口前最近邊界的殖民區。我們在那裡下車,改騎馬前往,我也向一路陪我們來的丁明宜(Tin Ming Yi,譯音)將軍道別。看到我要走了,他似乎真的感傷。我想他是確信那些外國的帝國主義者、間諜、復仇者以及共黨神殿中的其他惡魔會危及我的生命。他和張將軍採取同樣的陣線,警告我要小心,他還要我向碰到的反革命分子說明自『解放』以來,西藏的長足進步。如果他們不相信,他說,他們可以回來,自己親眼看看。我向他保證會全力以赴。說完之後,就轉身騎上小馬,開始我的漫漫雲中路。在那座隘口的最高點,矗立一座很大的圓錐形石堆,上面插著彩色的祈禱幡。我們依照習俗,每人都給石堆加一塊石頭,並且高喊『拉給羅(Lha Gyal Lo!意即諸神勝利)』。之後,我們才走向山下的錫金王國。 在山的另一邊、就在隘口下面,我們在雲霧中遇見一列歡迎的行伍,包括一些官員和演奏著西藏和印度國歌的軍樂隊。其中一位是前印度駐拉薩領事阿帕.B.潘特先生(Mr. Apa. B. pant),他現在是駐錫金的政治官員。同來的有蘇南.托結.卡日(Sonam Topgyal Kazi)他是錫金人,整個訪問過程中,他一直擔任我的翻譯。當然我的朋友錫金皇太子通篤.南結也來了。 從邊境一路上到聰哥湖畔的小聚落,都由他們護送。當晚我們就住在那裡。現在天色已暗,氣候又冷,地面上積了厚厚的雪。抵達時,我真是非常驚喜---好幾年沒見過面的塔澤仁波切和嘉洛通篤都在那兒歡迎我。羅桑桑天和年幼的天津秋吉也隨我一起出來旅行,所以這是我們一生中,五位兄弟首度團圓。 第二天,我旅行到錫金首都岡托。剛開始是騎小馬,接著改坐吉普車,最後一段路是坐貴賓車。這時我見到錫金的摩訶羅----塔希南結爵士,我們就是坐他的車子。接著,發生一件好笑但轟動的事情。我們進入岡托時,整個衛隊被聚集的人群困住了。無數民眾,包括許多興奮的學童,從四面八方擁來,投擲哈達和鮮花,使我們無法前進。突然不知那裡跑來一位不知名的年輕中國人,扯下在車子這一邊和錫金國旗相對的西藏旗子,換上中共的旗子。 我們在岡托停留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就前往巴格多扎飛機場(Bagdogra)。我記得這不是段令人愉快的旅程。從拉薩出發到現在,我已經很累了。此外,前天晚上我還參加了國宴。尤其令人喪氣的是,早餐吃的是麵條;接著車子下行向印度平原,車裡面熱得我透不過氣來。飛機正在等著我們。這架飛機比我訪問中國時所搭乘的那架舒適多了。我們坐飛機到阿拉哈巴得(Allahabat),我們在那裡休息,然後再到新德里的帕蘭機場(Palam)。當飛機飛在人煙稠密的印度城鄉上空數千英尺高處時、用膳,我在沈思印度與中國如此大不相同。我從沒有到過印度,但是我已經察覺到兩國的生活方式差距甚大。不知道什麽緣故,印度似乎更開放、自由自在。我們到印度首都後,更增強了這個印象。一大隊的儀隊在等著我們,那兒還有首相尼赫魯先生、副總統羅達庫里夏那先生。這裡的表演、儀式比我在中國所看到的還要多;同時,他們所說的每個字,不管是首相致歡迎詞時說的,還是地位較低的官員所說的,都有一種誠懇的成分。人民都說出他們真正的感受,而不是說他們認為他們應該說的話。他們不矯飾。 我從飛機場被直接帶到總統宮邸(Rashtrapat B havan)去見印度總統拉伽德拉普拉薩德先生(Dr Rajeendra Prasad)。我發現他相當老,行動遲緩,人非常謙恭。他和身旁穿著亮麗軍服的高大副官、神氣的貼身侍衛比較起來,顯得非常巨大。 第二天,我到雅木納(Jammuna)河畔的拉雅黑(Rajghat)朝聖。聖雄甘地就是在這里火葬。這是個寧靜而又美麗的地方,在那兒我覺得非常高興。像我這樣遭受異族統治的外賓,在這個曾採用過Abimsa的國家中,也覺得心情愉快。 Abimsa就是聖雄甘地的『非暴力主義』。當我肅立祈禱時,我感覺悲欣交集,難過的是我沒能親自見到甘地,高興的是他的一生是非暴力主義的輝煌例證。對我而言,他是個完美的政治家,他把利他的信仰放在任何個人打算之上,我也確信他這種對非暴力目標的奉獻,是管理政治的唯一方法。 以後幾天是佛陀誕辰的慶祝活動。在這段期間,我說到我相信佛陀的訓示不僅可以將個人的生命導向和平,它也可以給國與國之間帶來和平。我也利用機會和許多甘地的信徒討論印度是如何以非暴力的方式來完成獨立。 此時,我在印度的一個主要發現是:雖然我常常被邀宴,但是這些宴會、接待卻比我在中國所參加的要來得粗簡多了,會場裡瀰漫著誠懇的氣氛,這意味著真正的友誼有機會發展。這和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驗形成強烈的對比。在中國,可以靠著威勢欺凌,使人改變心意。我現在可以比較、並且親自看到:這是錯誤的想法。只有籍著彼此尊重的滋長、以真實的心相對待,友誼才會產生。只有靠這些方法才有可能打動人心,武力是絕不可能的。 這些觀察使我想到一句西藏的老諺語:犯人一旦逃掉,就不會再回來,我開始考慮是否留在印度。我決定在和尼赫魯班智達會面時,仔細查詢尋求政治庇護的可能性。稍後我很快的作過試探。 事實上,我在好些場合裡見到尼赫魯首相。他是個高大、漂亮的男人,他頭上戴的甘地小帽把他的北歐面孔襯托得更加明顯。和毛澤東相比,他是顯得沒那麽『自信』,但是他不獨裁。他看起來是個誠實的人這就是為什麽後來他會被周恩來給騙了。我們第一次會面時,我就利用機會向他詳細說明中共如何入侵我們和平的領域,我們是如何措手不及地面對敵人,當我知道的外面的世界沒有人準備承認我們正當的獨立權利時,我是如何忍辱負重去配合中國。 起初他禮貌地聆聽、點頭。但是我猜想這篇感情豐富的演講對他來說是太長了。隔了一會,他顯得分心,就好像快要打瞌睡了。最後他注視我說,他了解我所說的。 『但是你必須知道,』他有點不耐煩的繼續說:『印度不能支持你。 』當他以清晰、漂亮的英語說話時,他的長下唇好像同意他說的話似的抖動著。 這是個壞消息,但不完全出乎意料。雖然尼赫魯現在已經表明了立場,我仍然繼續說,我正在考慮流亡印度。他再次反對:『你必須返回你的國家,以十七點協議為基礎,試著和中國共事。 』我抗議說我已經試著竭力去作,但每一次我以為我已經和中共當局達成諒解時,他們總是粉碎我對他們的信賴。現在東藏的形勢大壞,我害怕一場強力的、兇暴的報復,會摧毀整個國家。我怎麽還可能相信十七點協議能行得通?最後,尼赫魯說他會親自跟周恩談這件事。周恩來當時在德里,隔天他就要去歐洲了。尼赫魯也要安排我會見周恩來總理。 尼赫魯真的說到做到,第二天早上,我隨著去帕蘭機場;他安排我在當天傍晚會見周恩來。我們再度會晤時,我發現我的老朋友和記憶中一樣,充滿了魅力、笑容和欺騙。但是我不理會他唬人的禮貌。相反地,我相當率直的告訴他,我關切中共當局在東藏的暴行。我也指出我注意到在中國政府系統與印度國會之間有明顯的差異:印度人民能自由表達他們真正的感覺;如果認為需要的話,他們也可以批評政府。就像以往一樣,周恩來在說順耳話以前,總是小心地傾聽。 『你只有在開第一次大會的時間到過中國,』他說:『第二次大會已經召開,每件事都已經改變得不可能再更好。 』我不相信他,但是跟他吵也沒有用。接著他說他聽到我考慮留在印度的謠言。這是錯誤的,他警告我。我的國家需要我。這也許是真的,但是我忘了我們這次談話並沒有解決任何問題。 我的兩位兄長----塔澤仁波切和嘉洛通篤也會見了周恩來,或許應該是『Chew and Lie』(耍嘴皮和撒謊)---他停留德里期間,印度的一家報紙這麽稱呼他。我的兩位兄長甚至比我還坦率,雖然周恩來懇求他們回去,但是他們告訴周恩來,他們一點也不想回拉薩。同時,我也終於開始到印度的各個聖地朝聖,在朝聖期間,我試著把政治從我的心中拋開。不幸,我發現我不可能把擔憂國家命運的想法抖落掉。班禪喇嘛陪我到每個地方,他不斷在提醒我們的可怕處境。他不再是那個曾經認識的仁慈、誠懇的孩子;中共的長期壓力已經對他年少的心造成不可避免的影響。 在從桑奇(Sanchi)到厄強塔(Ajanta),然後到菩提伽耶和鹿野苑的路上,當我能夠把自己完全投入深深的喜悅與崇敬時,我發現有些時候自己已經回到心靈的家園。每一件事物都有些相似。 在比哈爾(Bihar),我訪問了那爛陀---它曾經是最大、最有名的佛教大學所在地,但是已經破敗數百年了。許多西藏學者曾在這兒研讀。而現在當我看到昔日曾是某些最深邃的佛教思想的發源地,而今卻是殘柱碎石的淒涼景象時,我再次地見到『無常』是多麽的真實! 最後我到達菩提伽耶。來到這個佛陀成道的地方,我非常感動,但是我的快樂並沒有持續多久。在菩提伽耶時,我收到我的中國衛士所傳達的訊息:周恩來回到德里,他想要見我。然後在鹿野苑,我收到一封由張經武將軍拍來的電報,他要我立刻返回拉薩。電報中說,意圖顛覆的反革命分子和里通外國的帝國主義者正在計劃一樁暴動。我必須要立刻趕回去。 我坐火車回德里,在火車站見到了中共駐印度大使。他堅持要我和他一起坐他的車子回大使館,這項舉動使我的管家、貼身侍衛覺得驚恐;我就在大使館裡見到了周恩來。管家和貼身侍衛都怕我被人綁架,他們到達大使館時,他們無法確定我是否真的在那裡,所以就請一個人拿了件毛衣給我,看看他們的反應如何。同時,我和周恩來作了一次坦率的討論。他告訴我西藏的形勢已經變壞了,他們指出中共當局準備要使用武力粉碎任何民眾的反抗。 此時,我又坦率地告訴周恩來我關切中共在西藏的所作所為,雖然中共曾明確保證,他們不會這樣做,但是仍然強把改革加諸於我們西藏人身上。他極具魅力的回答我。毛主席曾聲明至少在最近六年不會把任何的改革引進西藏。如果六年之後我們仍然沒有準備好,如有必要,他們會延緩五十年。中共來西藏只是想幫助我們。我仍然不相信周恩來的話。周繼續說,他知道我正計劃去噶林邦訪問。這倒是真的。有人請我對那兒居住的西藏人傳法。他以強烈的語氣勸我不要這麽作,因為噶林邦充滿了間諜和反革命分子。他又說我應該提防那些我所信賴的印度官員,有些是好人,但有些是危險的人。然後他改變話題。他問我要不要準備回那爛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的身分參加迎請中國高僧唐玄奘舍利、文物的法會。我得知尼赫魯班智達會出席這次集會,我接受了。 再度見到尼赫魯首相時,他隨身帶了一份十七點協議。尼赫魯又力勸我返回西藏,以『協議』為基礎和中共共事。沒有選擇的餘地,他說,他必須明白表示印度不會幫助西藏,他也告訴我,我應該照周恩來所說的去做,並且返回拉薩,不要在噶林邦停留。但是當我堅持要去噶林邦傳法時,他突然改變心意。 『畢竟印度是個自由的國家。 』他說:『你不會違犯印度的法律。 』接著他答應幫助我打理這次訪問一切必要的安排。一九五七年二月,我帶著少數隨員坐火車去加爾各答。我記得在路上,我的母親渾然不知任何限制,也不覺得拘束,她帶了一個小爐子,煮了一些非常美味的tbugpa(一種傳統的西藏麵湯)。我們到達西孟加拉首邑之後,停留了好幾天,才坐飛機到北邊的巴格多扎---喜馬拉雅山的小山丘就是在這裡從濕熱的廣大印度平原急速地向上攀高。我們最後的一段路是坐吉普車。我們到達噶林邦時,我下榻在一個不丹家族的房子,我的前世流亡印度期間一度住在這裡。他們讓我住在達賴十三世住過的房間。在相似處境下住在同一件房間,這實在是一種奇異的經驗。這個非常友善的家庭是不丹首相家族的一支,不丹首相稍後遭人暗殺。這個家庭有三個小男孩,最小的男孩對家裡的客人極有興趣。他一直跑進我的房間,好像要調查我似的。然後咯咯的笑,順著樓梯又滑下去。 我到噶林邦不久就見到我的首任首相魯康瓦,他假裝朝聖,最近才從拉薩來到噶林邦。我非常高興能見到他,雖然我很快就發覺他完全反對我回拉薩。我的兩位兄長同樣也來到噶林邦,他們同意魯康瓦的看法,開始勸我留下來。這三個人也請噶廈不要讓我回去。在菩提伽耶時,我的兄長們曾和一些同情西藏的印度政治家接觸,其中之一就是賈雅.普拉卡處.那惹顏(Jaya Prakash Narayan),他答應以後在一些恰當的時機裡,發出印度支持西藏爭取自由的聲音。我兩位兄長、魯康瓦和其他一兩位人士都確定當支持西藏的聲音出現時,尼赫魯會被迫支持西藏獨立。畢竟,搞得中共陳兵印度北方邊界,對印度沒有好處。但是我不相信。我問隨員之一的嘎波嘎旺吉美(被中共強迫簽訂十七點協議的西藏代表團團長)他的看法怎麽樣?他的忠告是,如果有可能發展出一套明確的計劃的話,那麽就值得考慮留下來。但是目前沒有任何事情是具體的,他覺得除了回去以外,我別無選擇。 我請示神諭。達賴喇嘛可以請教的神諭有三位。其中的兩位----涅沖和噶東就在我身邊。他們兩人都說我應該回去。在我請示神諭的時候,魯康瓦闖進來了,神諭對他擅自闖入生氣了,神諭告訴他留在外面,好似神諭已經知道魯康瓦已經下定決心似的。但是魯康瓦不管他,仍然照樣坐下來。之後,他走過來對我說:『當人遇到危難時,人就問神;當神遇到危難時,他們就說謊。 』 我的兩位兄長堅持我不應該回西藏。他們就像魯康瓦一樣都是有力量、有說服力的人。但是他們都不了解我的疑慮。他們相信:眼前西藏人就生活在中共的威脅下,所以要用任何可能的方法來對抗中共。他們認為最好的對抗方法就是我留在印度。這樣一來就有可能尋求外國的支持,他們確信如此易於得到外國的援助。他們認定美國會幫助我們。 雖然當時沒有談到以武力對抗中共,但是我的兩位兄長卻瞞著我和美國中共情報局訓練一些西藏人打游擊,然後再把他們空降入西藏。當然我的兄長們認為不讓我知道這件事會比較好。他們知道我會作什麽反應。 當我解釋,雖然我可以明白他們所說的理由,但是我不會採納,嘉洛通篤開始顯現激動的樣子。他是我的兄長中最激烈的愛國者,現在依然如此。他的個性很強,而且很固執。但是他的心不錯,母親過世時,他是我們兄長裡面最難過的一個。他嚎啕大哭。塔澤仁波切比嘉洛通篤溫和一些,但是在寧靜、和氣的外表下,卻藏著倔強、不屈服的心。在危機中,他表現不錯,但是現在他也露出惱火的樣子。最後,沒有人說服我,我決定依據尼赫魯的忠告和周恩來的保證,返回西藏,給中共最後一次機會。 離開噶林邦後,我被迫留在岡託一個月;之後我才能再次橫越那簇隘口。但是我一點也不懊悔,我利用這個機會對當地民眾傳法開示。 最後,一九五七年三月。我懷著一顆沈重的心,啟程回拉薩,羅桑桑天在最後一分鐘決定留在印度,使我更加憂愁,最近他動過盲腸手術,身體狀況很差。我到達邊境,向我的印度朋友揮別時,他們都哭了,我心情更是往下沈。在彩色的西藏祈禱幡之中,至少有十二面血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旗子。當秦毫漢將軍(Chin Rhawo rhen,音譯)過來見我時,一點也沒辦法讓我好過一些。因為雖然他是個善良、誠懇的人,但是我總是不禁想到他所穿的軍服,而不是『解放』。 |
| © The Office of His Holiness the 14th Dalai Lama. e-mail: service@dalailamaworld.co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