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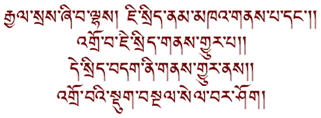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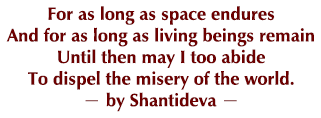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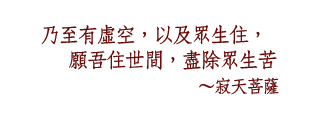 達賴喇嘛格言
每當憤怒即將爆發之際,你可以訓練自己用不同的角度來看待憤怒的對象。任何可能引發你憤怒情緒的人或情境,基本上都是有關連性的;從某個角度來看,它讓你生氣,但若由其他觀點審視,你可能發現其中自有美意。
相關連結
|
藏曆:2152 木蛇年
⌘ 流亡中的自在 ⌘
第三章:入侵--風暴開始
一九五○年夏天,就在藏劇節慶之日,有一天,我正好在諾布爾卡宮,甫從浴室走出,發覺腳底下的地開始在動。已是深夜,我正和一位隨從閒談,並一邊進行睡前盥洗。盥洗室位於住處幾碼外的附屬小屋裡,所以地震時,我正在室外。首先,我想到我們一定還會再碰到另一次地震,因為西藏位於地震頻繁的地帶。
既已十分確定,我一回到室內,就注意到好幾副掛在牆上的書已東倒西歪。隨之遠處發生一起可怕的災秧,我再度衝出去,後面跟著好幾位潔役。我們仰望天空,一陣接一陣的轟隆聲相繼而起,似乎是砲彈。我們猜想這就是震動和轟隆聲的肇因:可能是西藏軍方正進行某種演習。總共約有三十到四十次爆裂聲。 翌日,我們才知道根本不是軍事演習,而的的確確是某種自然現象,有些人甚至看到一道怪異的紅光,從爆破聲源方向的天空射出。它逐漸形成,幾乎全藏的人都看得到:東到幾乎四百英里遠的昌都,西南方三百英里外的薩迦。我聽說實際上發生在加爾各答。隨著這件事情的真相逐漸沉寂,人們自然開始認為這不只是地震,而是個預兆。 從很早以前開始,我就一直對科學深感興趣。所以很自然地,我希望為這件異象找尋科學依據。幾天后,我遇見哈勒,詢及如何解釋此件異象;不僅是視之為地震,更重要的是視為殊異的天象。他說,他確定這兩者相關。一定是整個山脈的上升作用造成地殼的爆裂。 對我來說,這個說法似乎可信,但不盡然如此。為什麼地殼的爆裂以一陣伴隨著轟隆聲的夜空光亮顯示?何況,隔著如此無窮盡遙遠的距離,如何能為人目睹?我不認為哈勒的說法能說明一切。直到今天,我還是如此認為。或許科學另有解釋,但我覺得,這些異象超乎科學,屬於某些真正神秘的領域。在這個個案中,我發現接受『目睹之情景為超科學現象』的說法,較為容易。無論如何,從高空或僅是地底發出的隆隆聲警告,暗示了西藏的處境將迅速惡化。 異象就在藏劇節慶之前發生。兩天以後,這個預兆(假如它是的話)開始被賦予實象解釋。一直到晚間,表演正在進行當中,我發現一名傳訊人朝我跑來。一直到帳下,他突然轉向攝政塔湯仁波切,他坐在帳裡的另一邊。我驀地警覺事情不妙。在正常的情況下,公事都必須等到下個星期才會處理。我好奇到幾乎忘形。這是什麼意思,一定會發生什麼可怕的事情。然而我是個小孩,又沒有政治權力,我必須等待,直到塔湯仁波切酌情告訴我究竟怎麼一回事。不過,我早已發現另一個實時得知的妙方:我站在一個有抽屜的櫃子上,透過分隔我們房間牆上的高窗窺視。當傳訊人到的時候,我往上蹬起,屏息偵察攝政的舉止。他讀信時,我可以清楚地看清他的臉。他臉色肅穆。好幾分鐘後,他才稍展神色,我聽到他下令召集內閣。 我又發現這封信事實上是在昌都的康省省長打來的電報,敘述一起堡壘遭到中共軍人突襲的事故,主事的軍官陣亡。這的確是件重大新聞。早在前一年秋天,那裡即遭中共越境入侵,他們高舉將西藏從帝國主義侵略者手中解放的意圖不管那可能意味什麼。儘管事實上,所有拉薩的中國官員已經在一九四七年被驅逐了。 而現在看來,中共似乎足以肇至威脅。果真如此,我十分了然藏人正陷入重大險境,因為我軍總共不到八千官兵,遠非新近奪得政權的中共人民解放軍的對手。除了心頭充滿悲傷,我不太記得那年藏劇節還發生什麼事。甚至最奇妙的舞蹈演出,鼓聲節奏放慢,也不能吸引我的注意力;他們皆著精緻的妝扮(有些穿著像骷髏,表示死亡),莊嚴而合拍地依照古代的舞步舞動。 二個月後,十月,我們極端的恐懼達到頂點。消息傳到拉薩,一支八萬人的中共人民解放軍隊伍已經穿越昌都東邊的翠處河。中國廣播宣稱,中共建國一周年,開始『和平解放』西藏。 所以,斧頭已砍下。再不久,拉薩勢必淪落。我們不可能抵禦這樣的屠殺。除了缺乏人力,西藏軍隊的困境是擁有的現代武器太少,而且幾乎沒受過訓練。整個攝政時期,完全忽略這些。儘管一些特定軍團從駐地匆忙開拔,新的一支又招募齊了。由於歷史背景影響,藏人基本上愛好和平,從軍被視為最低下的生活形式:軍人被視為屠夫,派去與中共短兵相接的軍隊素質並不高。 去推測事情可能的結果,否則情況會改觀等等,皆無補於事。不過,仍要說明的是,中共在進攻西藏時,大量損兵折將。在某些地區,他們遭逢強悍的抵抗,除了戰爭的直接為害,他們的難題大部分是捕給不易,以及惡劣的天侯。許多人死於飢餓,其它的大抵也難逃高山症的考驗。這種病總是折騰外來客,有時確能致人於死。至於這次戰爭,不管西藏軍隊數量多大、裝備再精良,結果其努力終將赴東流。因為,即使中國的人口都比我們多上一百倍。 這個威脅西藏自由的舉動,並非沒有引起世界的注意。在英國政府的支持下,印度政府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抗議,並聲明中共入侵,對和平無益。一九五○年十一月七日,西藏噶廈及政府向聯合國求援,盼其代表西藏出面調停。但是,不幸地,西藏依照其和平孤立的政策,從未尋求成為聯合國的一員,而且未曾致力於此除了在年底前發出兩份電報。 隨著冬天逝去,局勢越來越壞,要達賴喇嘛即位之說甚囂塵上。人們擁護我全面掌權的行動開始出現距離正常秩序,我還得等兩年後。據說海報貼滿拉薩市,批判政府,呼籲我立即即位;還有一些歌也有同樣的訴求效果。 有兩派立場:其一是視我為危機中的領袖;另一些人則認為要負擔這樣的責任,我還太年輕。我同意後者的看法,不幸的是,我沒有共同商量的機會。政府決定將之付諸神諭。這是非常緊張的場合,最後靈媒頂著他那巨大的、儀式用的頭飾,蹣跚搖擺地踱到我座前,獻上一條白絲貢巾(哈達),放在我的膝上,並說『他的時代到了』。 扎滇金剛( Dorje Drakden)已經明示了。塔湯仁波切立刻準備從攝政位置退下來,他仍舊是我的資深親教師。剩下來的就是占卜國師挑選即位日期的事了。他們選中一九五○ 年十一月七日,因為這天是年底前最吉利的日子。這樣的發展令我非常沮喪。一個月以前,我還只是無憂的年輕男子,熱切地期盼一年一度的藏劇節。如今我要面對這樣緊迫的景象:在國家準備開戰時,領導我的國家。但是,在回溯中,我知道這不是突如其來。迄今好幾年來,神諭對政府顯現出公然的輕忽,對待我卻十分禮遇。 十一月伊始,大約在即位典禮前兩週,我的大哥來到拉薩。我幾乎認不得他。如今他是塔澤仁波切古本寺的主持。我被認證為達賴喇嘛的轉世時,曾在古本寺裡過了一年半初始的寂寥生活。當我定睛看他,我知道他受了極大的苦。他陷入一種可怕的狀態,非常緊張焦慮。他在告訴我過程時,甚至口吃。我們兩個的出生地,也是古本寺所在地——安多,比鄰中國,很快地落入中共的掌握中。他立刻受縛監禁。喇嘛的活動都受到限制,而主持本人卻淪為罪俘,被關在寺裡。同時,中國人全力對他洗腦,用新的共產主義者的思考方式,試圖改造他。他們有個計劃,如果塔澤仁波切願意勸服我接受中共統治,他們會讓他自由前往拉薩。如果我拒絕,他就殺了我,他們隨後會酬報他。 那真是個怪異的提議。第一,任何殺生的念頭對佛教徒皆是離經叛道的。所以這個要他為了個人私利,而暗殺達賴喇嘛的建議,顯示中國人對西藏人性格了解之膚淺。 經過一年,其間我大哥目睹自己在家園遭中國人顛覆,他逐漸了解他必須逃到拉薩來警告我以及西藏政府,如果中共進攻,我必須貯存糧食。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假裝馴服,所以他終於同意照他們的計劃行事。 他喘著氣告訴我經過。一直到現在,我對中國人幾乎一無所知。而對共產黨我更是幾近完全無知,儘管我知道他們曾經嚴厲地迫害蒙古人。除此,我所知僅是手邊剛巧看到的過期的美國《生活》雜誌。但是我大哥現在明白告知,他們不僅是無宗教主義者,事實上也反宗教之道而行。塔澤仁波切告訴我,我們唯一的希望是得到外國的支持,以武力對抗中共。我聽了,非常害怕。 佛陀禁止殺戳,但是指出在某些情況下,可以不得已而為之。而按照我大哥的想法,當前的狀況正是如此。因此,他要破了僧戒,脫下僧服,以西藏特使身分出國。他希望與美國聯繫。他覺得他們當然會支持讓西藏自由的想法。我乍聞之下,嚇得一驚,但是在我反對之前,他警告我離開拉薩。雖然有許多人也提這件事,並沒有多少人持這樣的觀點。但我大哥懇求我接受他的建議,不管大多數人怎麼說。他說,我的處境危殆,絕不能冒落入中共手中的風險。 我們會面過後,大哥在離開拉薩前,和許多政府官員討論過。我和他再見過一、二次,但無能勸服他改變心意。他在過去一年來的可怕境遇使確信已經沒有別的路可走了。我沒細想這些事情,而全神貫注在自己的事情上。還有幾天,即要舉行我的即位 大典。 為了紀念這個典禮,我決定全面大赦。當天,所有獄囚都會被釋放,意即蕭村的監獄將會一空。我很高興有機會如此做,雖然也有懊悔的時候。回想當年與獄囚之間似有若無的友誼,我不再擁有這種樂趣了。當我在庭院中透過望遠鏡遙望蕭村,我看見監獄裡空空如也,除了幾隻狗覓食殘渣。那一剎,彷彿有一些東西從我生命中消失了。 十七日的早晨,我比平時早起一、二個鐘頭,天色仍黑。著衣時,我的服飾總管交給我一件繞在腰上的綠巾。這是按照占卜國師的指示,他認為綠色是吉祥色。我決定不吃早餐,因為典禮冗長,我可不想被任何生理訊號干擾。不過,占卜國師堅持在典禮開始前,我必須吃一個蘋果。我記得那真是難以下嚥。諸事妥當後,我到佛堂,破曉時,即位典禮將在此地舉行。 這是個政府官員全員到齊的場合,還有各外國駐拉薩官員隨同壯聲勢,大家都穿上最正式、最絢麗的華美服飾。不過,當時天色很暗,我無法看個仔仔細細。典禮中,我接受象徵承擔世俗權力的金輪。我記得不太多,只除了一陣強勝一陣的釋放膀胱尿液的急迫需要。我責備占卜國師。他們要我吃蘋果的主意無疑是問題的根源。我對他們從沒有太大的信心,而這次又強化我的壞印象。 我總覺得一個人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如生與死,不必聽占卜國師的意見,不必勞動其它人。不過,這只是在下鄙見。這並不意味我認為藏人習慣的占卜實務應該中斷。從西藏文化的觀點而言,占卜是很重要的。不論如何,在這個場合裡,我的情況愈來愈糟。最後,我傳訊下去給侍衛總管,請他加快節目進行速度。但是節目繁冗,我開始害怕它永遠不會結束。 最後,節目終於結束。我發現自己成為統帥六百萬人民的當然領袖,面臨全面戰爭的威脅,而我只有十七歲。這是個難以自處的處境,但是我認為如果能盡各種可能避免這場災難,是我的責任。我的第一件任務就是提名兩位新總理。 提名兩名是源於西藏的政府制度,從總理以下的各個職位都是雙軌並行,每一個職位各由一名在家人與出家人擔任。這套制度由偉大的達賴喇嘛五世所創,他是首位在宗教領袖的職務外,兼攝世俗權力的『法王』。不幸的是,雖然這個制度在過去一直運作良好,是在廿世紀卻是毫無希望地不合時宜。除此之外,經過大約廿年的攝政時期,這個政府已是十分腐化,如我先前所述。 不消說,改革也從未進行過。即使是達賴喇嘛也無能為力;因為無論他提出什麼,首先,他必須照會兩位總理,然後是內閣,其次是行政部門的每一位成員,最後付諸國民大會。如果有任何人反對他的提案,這件事便很難再進一步發展。 改革由國民大會提出的時候,也會發生同樣的狀況;除非程序顛倒。比如一件法案最後提陳達賴喇嘛,也許他希望做點修正,在這種情況下,這些意見是寫在羊皮條紙上,釘在原先的文件裡,送回國民大會表決。但是他們深信各種外國影響會危及西藏佛教的恐懼心理,則是煽動性的改革難以推展的原因。 由於心理有底,我選了羅桑扎西作為僧官總理;另外選了乾練的俗官行政人員魯康瓦,作為相對的俗官總理。 諸事停當後,我決定和他們及內閣商議出訪美國、英國及尼泊爾的代表人選,希望說服這些國家代表我們和中共調停;另一方面,則派人赴中國協商撤兵。這些特使團直到年終才出發。之後不久,由於中共軍隊衛戌在東方,我們決定我應和最高級的政府官員移到南藏。這樣,如果情況惡化,我可以輕易穿越邊境,出亡到印度。同時,兩位總理依舊留在拉薩,我則帶著國璽走。 |
| © The Office of His Holiness the 14th Dalai Lama. e-mail: service@dalailamaworld.co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