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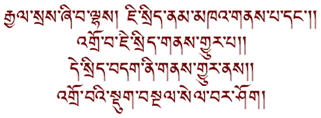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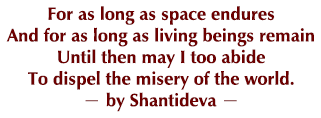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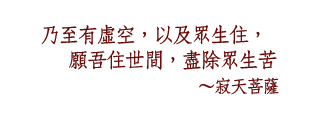 達賴喇嘛格言
所有宗教都在啟發我們的愛心、誠懇與誠實,如果太執著自己的信仰,而強迫他人接受,就會產生紛爭與煩惱。
相關連結
|
藏曆:2152 木蛇年
⌘ 流亡中的自在 ⌘
第二章:獅子法座
成為達賴喇嘛後第一個冬天的種種,我記憶不深。只有一件事讓我縈懷。在當年臘月除夕,南嘉寺的喇嘛照例要表演名為恰木(Cham)的儀式舞蹈(跳神舞會),象徵驅除過往一年的負面力量。因我迄未正式升座,官方認為我不適合到布達拉宮觀賞。桑天卻由母親帶著去了。我很豔羨。他當晚深夜回來,作弄地詳述濃妝的舞者騰空與猝然跳躍的動作。
再接著的一整年,即一九○四年,我仍留在諾布林卡,春夏月份間,我時常與雙親見面。在我被確認為達賴喇嘛之際,他們即取得貴族的地位以及可觀的財產,也可以在每年夏天使用諾布林卡宮園的村裡的一幢房子。幾乎每天,我習慣帶著一名隨從,溜去與他們相聚。這樣做並未全然獲准,但是負責管教我的攝政有時會放我一馬。我特別喜歡在午膳時間開溜,因為注定要成為和尚的小男孩,某些食物,如蛋與豬肉,必須忌口,我只有到父母家才能吃到。有一次,我正在吃蛋,正好被我的高級官員傑普堪布逮個正著。他非常震驚,我也是。我拉足了嗓門喊道﹕『滾開』。另一個場景是,我坐在父親旁邊,看著他嚼脆皮豬肉,象隻小狗注視著他,希望他分給我一些,他果真如此。豬肉的味道真是美。所以,總而言之,我在拉薩的第一年非常快樂。我尚未成為喇嘛,我的教育課程也還未開始。桑天也樂於游蕩一年,雖然他在古本寺已開始識字上學。 一九四○年冬季期間,我被送往布達拉宮,在那里正式升座成為藏人的精神領袖。關於這次典禮,我沒記起什麼特殊的,慶幸的是,這是我首度坐在希虛普恩錯格廳里的獅子法座上,那是巨大的、鑲滿寶石以及美麗木雕的寶座,廳名意指世間與出世間一切善行,這是布達拉宮東廂的主要包房。 不久以後,我被送往城中央的大昭寺,我在那里剃度成為沙彌。典禮包括剃髮儀式,從此以後,我削髮,並依僧制著茶色僧服。我當然不太記得典禮是怎麼回事,只記得,看到濃妝的慶典舞者的那一刻,幾乎忘我,不假思索地對桑天說﹕『你看!』 我的頭髮由西藏攝政瑞廷仁波切 ① 象徵性地剪掉一些。除了在我接掌大權之前擔任西藏最高領袖外,瑞廷也被指定為我的高級親教師。一開始,我小心翼翼與他相處,但我後來很喜歡他。他最引人注目的特徵是鼻子,連續有節。他充滿想像力,有一種相當自由的心性。他舉重若輕,不會過度小題大作﹕他愛郊游與馬,後來他和我父親成了好友。可惜的是,攝政的那些年,他成為備受爭議的人物。而此時政府已非常腐化,比如賣官鬻爵的情形已很普遍。 在我受戒時,流言紛傳他不適合主持剃度儀式。傳言他犯了色戒,不再是個和尚。另外,他責罰一位在國會上與他唱反調的官員,也招致公開批評。儘管如此,依照傳統,我去掉了原名Lhamo Thondup,冠上他的,Jamphal Yeshe,再加上前幾世達賴喇嘛,所以我的全名變成 Jampal Ngawang Lobsang Yeshe Tenzin Gyatso。 除了瑞廷仁波切是我的高級親教師外,我還有一位初級親教師塔湯(Tathag)仁波切。他是個非常脫俗的人,溫暖而且慈悲。我們一起上完課以後,他經常喜歡信口拈來地談話與說笑,我非常喜歡。最後,在我早年,尋訪團的領袖結昌仁波切,私底下也盡了不少心,形同第三位親教師。每有任一位親教師遠行,他替代他們的角色。 我特別喜歡結昌仁波切。他和我一樣,來自安多。他極為慈悲,我對他從來無法疾言厲色。在課堂上,為了逃掉我分內的背誦,我習慣鉤著他的脖子,撒嬌地說,『你背!』稍候,他警告崔簡(Trijang)仁波切,要特別注意不要笑出來,否則我鐵會吃定他。他在我九歲左右,成為我的初級親教師。 這樣的安排沒有持續太久。就在我的見習修行開始不久,瑞廷仁波切放棄攝政,主要是因為他的風評不佳。雖然才六歲,我仍被徵詢誰可以取代他。我指定塔湯仁波切,他隨後成為我的高級親教師;林仁波切則取代他,成為我的初級親教師。 塔湯仁波切是個溫和的人,林仁波切則非常自制且嚴厲,一開始,我的确很怕他。我甚至看到他的僕人就害怕,很快學會屏息辨聽他的腳步聲。但到最後,我很友善地對待他,我們發展出一種很好的關係。直到一九八三年往生,他一直是我最親近的知己。 如同我的親教師,另有三個人也被指定為我的貼身侍從,他們都是和尚,他們是儀式總管确彭堪布(Chopon Khenpo);掌膳總管索彭堪布(Solpon Khenpo);以及服飾總管堪惹天津 ②。天津也是尋訪團的一員,眼神銳利,我印象極為深刻。 我還很小時,與掌膳總管有一種親密的連屬感。這種感覺強烈到他必須隨時在我的視線所及之處;即使只從門口或室裡的門簾下看到他的袍子下襬也行。還好他很包容我的行徑。他是個很善良單純的人,幾乎是全然地無諱。他既不是說故事能手,也不是有勁的玩伴,但這些一點也無所謂。 對我們這種交情,我常常想一探究竟。如今看來,就像是小貓或某些小動物與其飼主之間的繫連。有時我覺得餵食的動作是所有關係的基本根源之一。 剃度成為沙彌不久,我開始接受基本教育。這教育祗是學習閱讀。桑天與我一起受教。教室我記得很清楚(一在布達拉宮,一在諾布林卡)。相對的兩面牆懸著兩根鞭子,一根是黃絲製的,另一根是皮製。前者是為達賴喇嘛預備的,後者是為達賴喇嘛的兄弟而設。這些體罰用的東西把我們倆嚇著了。只要師傅向那兩根鞭子望上一眼,就會讓我怕得顫抖。好在那根黃鞭從沒動用,那根皮鞭倒用過一兩回。可憐的桑天!他運氣不好,當起學生來不如我。不過,我懷疑他挨打也許是一句西藏古諺的作用﹕『打公羊,儆綿羊。』 儘管桑天和我都不許擁有同年齡的朋友,我們身邊卻總有人陪伴,不論在諾布林卡或布達拉宮,都有大群潔役人員以及內室照管者(不能稱為侍者)。他們大都是沒有受教或只受過一些教育的中年男子,有一部分是軍中服役後來此任職,職司保持房間整齊,監督地板務必擦過。這是我唯一講究之處,因為我喜歡在地板上溜冰。我和桑天在一起,惡形惡狀,他終於被送走,這些人就成為我僅有的陪伴。但他們真是不得了的玩伴!他們年紀也一把了,玩起來卻像孩子。 桑天被送到一所私立學校,我大約八歲。我當然很傷心,因為他是我與我家族的唯一聯繫。如今我只能在滿月時看到他。學校在滿月之日放假。每回會客完後,我站在窗前看著他離去,眼見他消失在遠處,心底梗塞著傷感。 除了與桑天每月固定的會面外,母親偶然的探訪便成我唯一的企盼。她總是由我姐姐多瑪陪著一道來。她們每回都帶來許多食品,所以我尤其喜歡他們來訪。母親是很棒的廚師,以烘焙精妙的點心著稱。 到我十幾歲時,母親也常帶著我的么弟天津秋結(Tenzin Choegyal)一道來。他比我小十二歲。如果有比我還調皮的小孩,那就是他。他最喜歡的遊戲之一是,帶著小馬上家里的屋頂。我記得很清楚,小小的他,有一回挨到我身上來,說母親新近向屠夫訂了一些豬肉。買肉可以,這樣買則是嚴禁的行為。預訂是不可以,因為如此一來,為了特別滿足你個人的需要,有些動物可能遭到殺戳。 藏人對食用非素食之物,采取一種比較戒慎的態度。佛教不一定戒肉,但是主張不應該為了吃肉而殺生。在藏地,吃肉可以,因為往往沒有什麼其它東西可吃(糌粑除外);不過,無論如何,不能介入屠殺行為。宰殺工作由其他人做。有些是由定居在拉薩的回人承擔。他們擁有自己的清真寺,自成一個繁榮的社區。全藏至少有數千名回人,其中約半數來自喀什米爾,其余則來自中國。 記得有一回,母親捎來肉食品塞滿米和剁碎物的香腸,是故鄉的特產,我立刻吃完,因為我知道如果讓任何一位潔役人員知道,勢必和他們分享。第二天,我病得很厲害。緊接著這次意外之後,掌膳總管幾乎丟差。塔湯仁波切認為他一定出了什麼錯,於是我被迫說出一切。這是一個很好的教訓。 布達拉宮雖然很美,但並不是個理想居所。西元七世紀,達賴喇嘛五世末期所建的布達拉宮,是位于一座名為『紅丘』石岩上的小建築。一六八二年,達賴五世圓寂時,布達拉宮大半仍未完工,所以,達賴忠誠的攝政德希桑結嘉措(Desi Sangye Gyatso)隱瞞他的死訊達十五年之久,直到完工。他只宣稱達賴要長期閉關。布達拉宮不僅是皇宮,垣內包括政府辦公室、許多儲藏室,還有南嘉(意即『勝利』)寺的一百七十五位和尚及許多佛壇,另外還有一所讓將來要成為澈炯官員的小和尚念書的學校。 我這個小孩得到達賴五世位於頂樓(第七層)的臥室。室內極寒,燈火不足,我懷疑從達賴五世圓寂後,那裡是否有人碰過。裡頭所有東西都是古老的、陳舊的;四片牆上掛的帘子後面積著數百年的陳灰。臥室一邊靠牆矗立著一座佛壇。上面放兩盞油燈(盛著腐臭油脂的碗裡,燭心燃著),還有小碟裝的食物以及淨水,供養菩薩。每天都有老鼠來掠食這些供品。我逐漸喜歡這些小生物。牠們非常好看,自行取用每日口糧,了無懼意。一到晚上,我躺在床上,總會聽到我這些同伴來回奔跑。有時牠們會到我床上來。這床是臥室裡,除了佛壇,以及一個裝滿座墊的木箱之外,唯一的實用家具。床以長的紅色帳幔圍住,老鼠也爬上帳幔,我蜷伏在毯子裡,鼠尿滴下來。 不論布達拉宮及諾布林卡,我的例行生活大抵相同,雖然在夏宮時,因為夏日白晝較長,作息表會提前一個小時。這無妨,我從未以日出之後起床為樂。我記得有一次睡過頭了,醒來發現桑天早在外邊玩著,覺得很生氣。 在布達拉宮,我習慣早上六點左右起床。梳洗打理好,作一段短短的祈禱及靜坐,為時一小時。然後,正好七時過後,我的早餐就送進來。早餐總是有茶及摻著蜂蜜或焦糖的糌粑。隨後跟天津開始上第一節課。從我學習閱讀以後,直到十三歲,這第一堂課都是書法課。藏文有兩種主要的書寫字體,『烏千』(Uchen)和『維美』(U-me),一種是用於手稿與官方文件,一種用於私人溝通。我只需學會寫『烏千』;但因學得很快,所以自己又學了『維美』③。 我回想這些早課,忍不住發噱。我在服飾總管注意的眼光下正襟危坐時,能聽到我的儀式總管在隔壁誦經。『教室』實際上是一個有成排盆栽的走廊,正好毗鄰我的臥室。天氣很冷,不過天色明亮,是研究 Dungkar 的大好時機。這是一種小而黑,鳥啄色彩鮮明的鳥,習慣在布達拉宮的頂上築巢。此時,我的儀式總管在我的臥室內晨禱。他誦晨課時經常睡著。每回他毛病犯了,就像斷電的留聲機逐漸消音,誦經聲慢慢消逝,愈來愈低,終至停止。停頓之後,直待他醒來,再度開誦。只是這時他會含糊帶過去,因為不知道自己念到那裡,所以經常一再重復好幾次。這種情形非常滑稽。不過,這樣也有好處。日後自己學到此段經文時,我早已了然於胸。 書法課後,照例是背誦課。只是學習佛經,當日稍晚再背誦。因為我學得快,所以覺得很無趣。饒是這樣,我通常又立刻忘了。 十點鐘是早課的休息時間。我當時還很小,也必須出席為政府官員舉行的會議。打從一開始,除了我全藏精神領袖的地位外,我即被培植有一天也成為西藏的世俗領袖。布達拉宮的會議廳正好在我臥室隔壁,官員從同一棟建築二及三樓的辦公室走上來。這些會議是很正式的場合,對各人朗念其當日的責任。有關我自己的案子自然也受嚴格檢視。我的侍從總管當結千嫫(Dongyer Chenmo)到我房間,領我到會議廳。我先接受攝政的問候,其次是四名核心內閣成員——噶廈依官階序列向我致敬。 朝會完畢,我回房繼續學習。我現在又有了一位初級親教師,我必須把當天背誦課學到的章節背給他聽。然後他把第二天要學的經文念給我聽,並且逐步詳析。這堂課持續到中午左右。此時,鐘聲響起(每隔一小時鐘響一次,只有一回,敲鐘的人忘了,中午一點竟敲了十三下)。中午也吹海螺。接下來是年幼的達賴喇嘛一天中最重要的節目﹕遊戲。 我很好運,擁有許多玩具。我還很小時,有位錯模(Dromo)地方的官員,這座城市與印度接壤,他常拿進口玩具給我,有時還附成箱蘋果。許多到拉薩的國外使節也餽贈禮物給我。我最喜歡的玩具里,有一樣是英國貿易使節團拉薩辦事處處長給我的麥肯諾(Meccano)牌全套鋼鐵組合的工學模型玩具。年歲日長,我得到更多套模型玩具;到十五歲左右,我已擁有最簡易到組合難度最高的所有麥肯諾牌套裝組合模型玩具。 我九歲時,二名美國官員組成的代表團來到拉薩。除了捎來羅斯福總統的信,他們還帶來一對美麗的嗚禽和一個華麗的金表。兩者都是很受歡迎的禮物。我對來訪的中國使節所送的禮物並沒有很深刻的影響;畢竟,小男孩對成匹的絹絲不會有興趣。 另一件最愛的玩具是發條裝置的火車組合,我還有一套很棒的鉛兵。等我稍長時,我學會將之熔化,改鑄為和尚。依照他們原先的用途,我還是喜歡把這些和尚佣置於戰爭遊戲梩。我常耗時把他們擺成陣勢,然後戰爭開始。只消數分鐘,我排的完美陣勢就亂成一片。這種情形也同樣發生在另一個遊戲上,那是糌粑麵糰或俗稱的粑(Pa)做成的小坦克形及飛機模型。 首先,我在成人友伴中舉行比賽,看誰能捏塑最好的模型。每個人分同樣大小的麵糰,比如說限定半小時內造出一個陸軍兵團。然後由我評定高下。比賽時,因為我夠機敏,總是不虞失掉場面。我往往淘汰做不好模型的與賽者。然後,我把我的部分模型給我的對手,換取其製造所費等量二倍的麵糰。如此這般,我總千方百計得到最大的實力,來結束比賽。同時,我在以物易物的交換中得到滿足。然後,我們開戰。至此,我事事順遂,在我全面落敗時也想一切如我意。正因我的潔役人員無論在何種形式的競爭,都從不放水。我經常試圖用我達賴喇嘛的地位來佔便宜,也毫無用處。我玩起來非常頑強,常常大發脾氣,還動拳腳,但他們照舊不讓步,有時就弄得我哭出來。 另一個我喜愛的把戲是軍隊操練,從一個鐘愛的潔役人員諾布通篤(Norbu Thondup)那裡學來的,他是大兵潔役中的一員。我總是像一般男孩充滿精力,離不開任何用肢體的活動。我喜歡一種明令禁止的特定跳躍遊戲。這種遊戲是盡可能地快跑,跑上一塊豎立大約四十五度的木板,然後縱身往前跳。不過,我這種侵略性的傾向,有一次差點給我帶來大麻煩。我在我前世的遺物中發現一個古舊、前端飾以象牙的輕巧短棒。我據為己用。有一天我拿著它在頭頂上用力甩,它忽然從我手中脫出,飛快打在桑天臉上。他咚一聲倒地。大約有一秒鐘,我確信我把他給害死了。暈眩過後,他站起來,淚如泉涌。右眉上可怖的縱深創口上血流如注。傷口後來受到感染,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才復原。結果,可憐的桑天臉上多了一個明顯的記號,跟著他一輩子。 一點過後,就是輕便的午膳。由於布達拉宮形勢使然,日光到中午才照亮全室,此時我的早課正好結束。但到下午二時,日光開始消褪,房間陷入陰影裡。我討厭這個時刻﹕每當黑暗再度吞噬房間,我心頭也拂過一片陰影。午膳以後,午課隨即開始。頭一個半小時包括我的初級親教師上的一節通識教育。他竭盡所能吸引我的注意力。我是個很難駕馭的學生,所有科目一概討厭。 我學習的課程和所有志在取得佛學學位的和尚相同。課程安排的極不平衡,在許多方面也完全不適合用來訓練廿世紀末葉的國家領袖。總而言之,我學習的課程涵括五個主要及次要學門 ④。前者是﹕因明學;西藏藝術與文化;梵文;醫學;以及佛學。最後一門最重要(也最難),可進一步分為五個領域:般若(Prajnaparanita),無上智慧;中觀(Madhyamika),觀想中諦的道理;戒律(毘奈耶 Vinaya),防止佛弟子邪非的法則;阿毗達磨(Abidharma),形上學;因明(Pramana),理則學;以及認識論。 五個次要科目是﹕詩;音樂與戲劇;占星學;度量與措詞 ⑤;同義字。事實上,學位的授予只以佛學、因明及辯證為基礎。因此,直到一九七○年代中期,我才學梵文文法。諸如醫學等基本科目,我至今只經過非正式的學習。 辯證學,或辯論的藝術,是西藏喇嘛教育系統的根本。兩個爭辦者輪流提問題,附帶要擺出規定的姿態。問題提出,質詢者右手高舉過頭,與伸出的左手??(此字不在電腦中,左邊一個“才”,右邊一個“府”字)掌,同時左腳跺地。然後右手滑離左手,指近對手的頭部。被詢問的人處于被動,專注心神,不僅要回答問題,還要駁倒對方,而對方無時不在繞著他走。在這些辯論中,機智是很重要的一環,如能以幽默方法將對手的主張化為已用,可得高分。辯論因此成為一種通俗的娛樂,甚至風行於不識之無的一般藏人之間;他們也許跟不上智性層面的嫻熟運作技巧,但仍能享受其中的樂趣與場面。過去常見游牧的流浪人和僻處拉薩之外的鄉野之人,費了大半個白日,在寺廟的庭院觀賞充滿學問的論辯。 一名和尚在這種獨特的論辯裡的能力,是評估其智性成就的指標,因此,作為達賴喇嘛,我不僅在佛學、因明學具備良好基礎,而且必須嫻熟論辯。我十歲開始認真研讀這些科目;十二歲時,兩位指定的辯證學專家(Tsenshap)⑥ 訓練我辯證的藝術。 午課第一節過後,下一個鐘點由親教師向我解說當天辯論的主題如何進行。四點用午茶,假如有人喝茶比英國人還多,那就是西藏人。根據最近我得知一項中國人統計的資料,西藏淪陷前,每年從中國進口一千萬噸茶葉。這項資料不可能正確,因為它暗示每名西藏人每年幾乎喝掉兩噸茶;這個杜撰的數據顯然企圖證明西藏對中國的經濟依賴程度,卻沒有列出我們喜歡喝茶的數據。 話是這樣說,但我並沒有完全分享我的同胞對茶的偏好,在西藏社會,傳統上習慣在茶里加鹽,用犛牛奶油取代牛奶的喝法。如果精心調制,會做成非常好而且營養的飲料,不過口味絕大部分要看摻和的奶油品質而定。布達拉宮膳房裡如常地供應新鮮的、乳酪似的奶油,而他們手釀的成品也很不錯。那是我真正樂享西藏茶的唯一時刻。今天,我大都採英國式喝法,早晚皆然。下午期間,我則光喝熱開水,這是一九五○年代我在中國養成的習慣。雖然白開水平淡無味,事實上卻非常有益健康。在西藏的醫療體系裡,熱開水被視為第一帖藥。 喝完茶後,兩位專長論證的喇嘛加人,此後的一小時多,我用來辯論一些抽象的問題,諸如,心靈的本質為何。大約五點半過後,一天的苦難終於到尾聲。我無法掌握確定的放學時間,如同一般藏人並不太有時間觀念;因此,一些人與事的起始與結束大多視情況方便而定。倉促向為禁忌。 親教師一離開,我立刻衝出,爬上屋頂。如果是在布達拉宮,我帶著望遠鏡。從附近的察克波里醫學院到遠處的聖城(拉薩的一部分),左近有大昭寺,俯瞰拉薩,景觀壯美。不過,我對位置遠在紅丘地下的蕭村興趣較濃。因為官方的監獄正好就在那里,而此刻也正好是獄囚放風的時刻。我把他們視為朋友,關切他們的一舉一動。他們也知道。每當他們看到我,就行五體投地大禮。我全認識他們,我也知道誰獲釋或又有新人犯來了。除了細察獄囚,我也習慣檢視放在天井的成堆柴薪和草料。 如是巡驗過後,就到有很多遊戲的時間,例如,晚膳之前的晚茶,在七時過後即送來。晚茶包括茶(無可避免)、蔬菜湯,有時加一點肉、乳果,再加上各種各類麵團,這些麵團甚為豐盛,由我母親烘焙,每星期新鮮地送來。我最愛的就是安多口味的小圓餅,外有硬皮,里面清淡而鬆軟。 我時常安排和一位或多位潔役人員共進晚膳。他們是老饕,全都是。他們的碗大得可以裝整茶壺的茶。其它時候,我和一些南嘉寺的喇嘛一起吃。 不過,我大都和三位喇嘛隨從,有時和契卡堪布(Chikyob Kenpo)——我的侍衛總管,一起吃。契卡堪布不在時,晚膳總是淪為喧鬧的場合,大家都很快樂。我尤其記得冬天的晚膳,我們傍著火爐坐,就著閃爍的油燈微光,喝熱蔬菜湯,一面傾聽外面風雪呼號。 吃過晚飯後,我蹬下七層樓梯,來到天井。我在那里必須邊走邊背經文和祈禱文。不過,當時我還小,始終漫不經心,幾乎從未照做,不是把時間花在想以前聽過的故事,就是在猜晚上臨睡前會聽到什麼故事。當然,這些故事本身有超自然的本質,所以嚇壞了的達賴喇嘛九點鐘就爬上那張黝暗、蝨蚤臭蟲肆虐的床。最恐怖的傳說是有一隻巨大的貓頭鷹專門在天黑後抓小孩。這個傳說源自大昭寺一座古代壁畫。因此,夜幕一落,我就非呆在室內不可。 由於青藏高原太高,許多其它地區流行的疾病在此從未聽聞。不過,還有一種經常出現的危險疾病﹕天花。我十歲左右時,有一名新來的、長得圓胖的指定醫生,使用進口的藥為我接種疫苗,以防染上天花。這是個非常痛苦的經驗,除了手臂上留下四個永久的疤,痛苦非常,我還發燒,持續大約二星期。我還記得大吐苦水,抱怨『那個胖醫生』。 我在諾布林卡和布達拉宮的生活都很規律,逢重要慶典或閉關時才有所不同。我閉關時,由我的一位親教師,有時是兩位,或者其它南嘉寺的高級喇嘛陪同。通常,我每年冬天閉關一次。一般而言,閉關長達三星期,期間我只有一堂短短的課,也不準到外面玩耍;只是在督導下長時期的誦經和打坐。我是個小孩,並非經常喜歡如此。我花了許多時間往臥室的各個窗口外望。向北的窗口面對色拉寺,群山為其背景。向南的這扇則面對大議事廳,我與政府官員的每日晨會在此舉行。 議事廳里掛了一組無價的、古老的刺繡書唐卡(Thang Kas),描繪藏人最喜愛的宗教導師之密勒巴尊者的一生行誼。我常注視這些美麗的圖書。如今,它們不知道遭遇如何。 閉關期的傍晚比白日更難捱,因為這正是與我年齡相仿的男孩騎在牛背上回到布達拉宮山麓瀟村家中的時辰。我至今記得很清楚,夕照逐漸淡褪,男孩子從附近的牧場歸來,引吭歌唱,我在靜默中坐著,口中誦著咒語(Mantras)。我常常希望能和他們易地而處。不過,慢慢地我逐漸也能欣賞閉關的好處。現在我真的希望有更多的時間閉關。 我因為學習能力強,基本上我與所有親教師都處得很好,我置身西藏某些『超級學者』間,我發現我心智能力還不錯。不過,大多數時候,我只是為了免得麻煩上身,才努力學習。然而,終於有一天,我的親教師開始憂慮我的進步速度。所以,天津想出一場模擬考試,讓我與我最鐘愛的潔役人員諾布通篤競試。我全然不知天津已在試前向他做過完整的解說,結果我輸了。這屈辱是公開的,尤其難堪。 欺瞞的把戲持續了一段時間,我非常用功,純然只是為了爭一口氣。但最後,我旺盛的向上心逐漸磨光,我又回到老樣子。一直到我接受專長教導後,我才了解教育有多重要,從此對功課才開始真正有興趣。現在我懊悔早年的懶散,每天總是至少用功四個鐘頭。有一件事,我想對我早年的學習生涯也許有所影響,那就是某些實際的競爭。因為沒有同學,我一直沒有任何對手可資以自我衡估。 我十歲左右,在我前世遺物中發現兩件古老的手搖電影放映機,以及幾卷底片。起先,找不到會操控的人。最後我們找到一位常住諾布林卡的中國老和尚,證實他是個精到的技師。一九○八年,達賴喇嘛十三世親訪中國。當時還是小男孩的老和尚,曾由父母帶著禮拜過達賴十三世。他是個極慈悲、誠懇的人,竭力盡瘁於其內心的宗教召喚,雖然他像許多中國人,脾氣很暴。 其中一卷底片是英王喬治五世加冕禮的新聞影片。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影片中的行伍,以及世界各地來的穿著華麗的士兵。另一卷則是充滿噱頭的影片,顯示一些女舞者如何從蛋里孵出來。最有趣的是一部有關金礦的紀錄片。從這份資料,我了解採礦是多麼危險的一種行業,而且礦工得在多麼困難的情況下工作。稍後,每當我聽聞有關勞動階級被剝削的問題(在往後的歲月裡,我時常聽說這種事),就想到這部影片。 我和這位中國老和尚很快成為好友,可惜的是,他在這事不久即往生。好在這段時間里,我已習得如何自行使用這部放映機,得到生平首度接觸電器的經驗,認識發電機的運用方法。這些經驗日後證實對我極有用處。後來我得到一件顯然是英國皇家送的禮物——一架附有發電機的現代電動電影放映機。這是透過英國貿易使節團轉達,貿易團副委員長福斯(Reginald Fox)親自教我使用的方法。 這段時間,我和另一位私人大夫,綽號列寧醫生,因為他蓄山羊鬍。他是個胃口極大的小個子,卻有極佳的幽默感。我尤其欣賞他說故事的本領。這二位醫生都接受過正統西藏醫療體系的訓練。關於西藏醫療體系,我在稍候章節會談一點。 我十歲時,打了五年的世界打戰結束了。對于打戰,我所知不多,除了終戰時,西藏政府派了一個使節團,到印度向英國政府致贈禮物與致賀。使節團由印度總督威福威爾爵士(Lord Wavell)接見。接下來幾年,我們又派一個代表團到印度,參加一個有關亞洲關係的會議。 就在那不久以後的一九四七年早春,發生了一件令人傷痛的意外,這件事情具體而微地顯示,上位者為圖個人私益,如何影響到國家的命運。 有一天,正當我觀賞一場論辯,我聽到槍聲響起,聲音來自北方色拉寺的方向。我衝到外面,滿懷興奮地欺望從望遠鏡中看到什麼。然而,在那當下,我也很難過,因為我知道炮火也意味著殺戳。結果竟然是六年前宣布退位的瑞廷仁波切,他決定奪回攝政權位,在一些喇嘛及下野官員的支持下,圖謀不利於塔湯仁波切。結果,瑞廷仁波切被捕,他的跟從者也死了不少。 瑞廷仁波切隨即解送到布達拉宮,他請求見我。不幸遭我的代表拒絕,不久之後就死於獄中。自然我尚未成年,我極少有機會介入司法事件;但是回溯過往,有時我覺得我在這個事件中也許可以盡些心力。如果我以某種方式介入,瑞廷寺——西藏最古老、美麗的寺廟之一,也許就可能避免破壞。總而言之,這整件事情非常愚蠢。儘管他犯了錯,我個人仍舊非常尊敬他,視他為我的第一位親教師以及上師。他死後,他的名字曾從我的名字里摘掉,直到許多年後,才奉神諭恢復。 那件令人傷感的事件發生不久,我隨塔湯仁波切到哲蚌寺及色拉寺(兩寺分別位于拉薩西方五哩及北方三哩半處)。哲蚌寺是當時世界最大的叢林,常住喇嘛逾七百人。色拉寺也沒小太多,有五百名。這次出訪是我的初次露面,擔任辯論者。我預定要和哲蚌寺三座學院及色拉寺兩座學院的方丈分別辯論。鑑於日來的擾攘,採取了額外的安全警戒,使我覺得不太舒服。此外,此生首度到達這個學習的高位階,我也覺得非常緊張。不過,無論如何,他們都對我很熟稔,我確信我的前幾世必與他們有所關聯。論辨當著數百名喇嘛大眾前進行,我雖不免緊張,幸好一切順暢。 大約在那段時間,我從塔湯仁波切那裡受領達賴五世的特殊祕法。這是達賴喇嘛獨傳的法,當初由偉大的達賴喇嘛五世(他至今仍名聞全藏)得之於一個異象。 這次傳法後,我有許多不尋常的經驗,特別是透過作夢的形式,雖然別人不認為有什麼大不了,我現在看來,卻覺得非常重要。 住在布達拉宮的一個補償是,那裡有數不清的儲藏室。對一個小男孩來說,房間裡的物件遠比房子有趣,那里頭有銀、金、無價的宗教文物;更有趣的莫過於我的每一任前世外層鑲有寶石的巨大靈塔。我尤其喜歡古劍、燧發槍、甲胃等武器收藏。但是即使這些,也無法與我好些前世擁有的不可思議的寶物相比。在這些寶物中,我發現一枝古舊的空氣步槍,完整地配備靶心與子彈,以及我已提過的望遠鏡;當然更別提成堆有關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圖解英文書籍。這些令我著迷,而且提供了我製作船、坦克、飛機模型的藍圖。等我年齡稍長後,我請人將其中部分翻譯成藏文,好理解其內容。 我還發現兩隻歐洲鞋。儘管我的腳還太小,我還是穿上,在趾端塞些碎布,多少可以將就。聽到包著鋼皮的沈重鞋跟聲時,我就覺得興奮。 孩提時我喜歡的把戲之一是,把東西分解,然後試著重新組合。我逐漸長於此道。不過,一開始時並非經常如願。我在前世遺物中找到一個古老的音樂盒,是帝俄沙皇送給他的,兩人素稱友善。音樂盒已闇啞,我決定修修看。我發現一條主發條壞得很嚴重,而且纏成一團,我用螺絲起子戳它,機身突然放鬆,發條無法上緊,所有發聲的細金屬碎片應聲衝出,碎片滿屋子打轉,造成的那種魔惑的噪音交響曲,我永生不會忘記。回思此次意外,深覺慶幸沒有失去一隻眼睛,因為我瞎修那機器的時候,臉十分貼近,以後我可能被錯認為以色列的戴揚(Moshe Dayan)將軍。 我非常感激達賴十三世圖登嘉措(Thupten Gyatso),因為他有很多有趣的禮物。布達拉宮現存的許多潔役人員服侍過他。從他們口中,我逐漸知道他生平若干事跡。我了解他不僅是道行高深的精神領袖,也是能幹且有遠見的世俗領袖。我又得知由於外國入侵,他兩度被迫出亡。第一次是一九○三年,英國派揚毫斯本上校(Young Husband)率軍入藏。 第二次是一九一○年的曼處斯(Manchus)。第一次,英國自動撤兵。但第二次,曼處斯的軍隊在一九一一至一二年冬天才被逐出。 達賴十三世對現代科技也深感興趣。他引入西藏的新事物中,包括一座電力發動的工廠,生產兩種硬幣及西藏首度發行的紙幣,還有三輛汽車,這是西藏的大事。當時,全藏幾乎沒有車輛運輸,即使馬拉的車子也完全沒有。他們當然知道有馬拉車這回事,但在氣候惡劣的藏地,馱獸是最實用的運輸方式。 圖登嘉措在其他方面亦同樣富於遠見,第二度出亡後,他安排把四位年輕藏人送到英國受教育。這個實驗成功了,留學生表現良好,甚至受到英國皇室接待,可惜後繼無人。如果這項計劃依他的初衷循序實施,我相信西藏今天的處境必然大不相同。 達賴十三世也把阻礙進步的軍事作了成功的改革,但也可惜人亡政息。他的另一項計劃是強化拉薩政府在康省的權威。他明知由於與拉薩迢隔,康省尤其不受中央行政當局重視。因此他提議將地方土司的兒子送到拉薩受教,學成返回,有政府授職。他也想鼓勵地方徵兵。不幸的是,由於慣性,他的計劃沒有一項實現。 達賴十三世的政治洞識也迥異常人。他在手書的遺囑中警告,除非發生急遽的變革,西藏的宗教與政府可能遭受來自內部與外部的攻擊,除非我們保護我們的家園,否則達賴與班禪喇嘛,父與子,所有這個信念的虔敬支持者,即將消失,湮沒無聞。喇嘛及其寺廟將遭摧毀。法律效力減弱。政府官員的土地及財產將被扣押。他們將被迫為敵人服務或讓家園淪落輾轉為丐幫。所有人類將沈溺於巨大的苦海及無邊的恐懼中;在苦痛中,日與夜過得特別慢。文中提到的班禪喇嘛,在西藏佛教里是僅次於達賴喇嘛的最高精神領袖,依照傳統,班禪駐錫在西藏第二大都市日喀則的扎什倫布寺。 就其個人來說,達賴十三世是個很單純的人。他廢除了許多舊習俗。比如,以前的慣例是不論何時,只要達賴離開他的寢室,任何正好在附近的侍從都要立刻離開。他覺得這樣的規定給大家帶來不必要的麻煩,使他不情願露面,於是他廢掉這條規則。 我還小時,就聽到關於他的許多故事,刻畫他是如何淳樸的一個人。其中之一是由一個很老的人告訴我的,他兒子是南嘉寺的喇嘛。那個故事敘及當時諾布林卡一幢新建築即將啟建,照慣例,許多民眾會在地基上放一塊石頭,以誌其尊敬與祝福之意。一天,有個從遙遠地方來的游牧人(說此故事者的父親)也來供養上石。他帶了一匹非常難駕馭的騾子,他俯身供養時,牲口隨即狂奔脫逃。好在有個人正從對面走來。這位游牧人大叫,要他幫忙抓住奔跑的騾子。這位陌生人照做了,並且把牠帶過來。游牧人先是高興,後即驚訝,因為給他援手的不是別人,就是達賴喇嘛他自己。 但是,達賴十三世也很嚴謹。布達拉宮和諾布林卡宮的花園都禁止抽洋煙。不過,也有例外的時候。偶爾他外出散步,行至石匠聚集工作處。他們沒有看到他,照舊彼此談天。其中一人大聲抱怨禁煙,說人又累又餓的時候,抽煙實在真好;不管怎樣,他要嚼些煙草。達賴喇嘛聽到這些,轉身即離開,沒有驚動大家。 但這並不是說他一向處事都慈悲為懷。如果我對他有任何批評的話,那就是我覺得他或許有些太獨裁。他對他的高級官員非常嚴厲,能為了極輕微的錯誤而嚴斥他們。他的慈悲限於對一般民眾。 圖登嘉措在宗教領域上的最大成就是致力提升寺廟的學術水準(全藏寺廟逾六千座)。為了達此目的,他賦予名位給最有能力的喇嘛,即使他們並不資深。他個人也為數千名沙彌授戒。迄一九七○年代,大多數高僧都從他受了比丘(Bikshu)戒。 二十出頭以後,我開始永久住在諾布林卡。在那之前,是在每年早春搬到諾布林卡;大約六個月後的冬天開始前搬回布達拉宮。辭別我在布達拉宮的陰暗臥室,無疑是我全年最歡愉的一日。此行通常以一個為時兩小時的儀式揭開序幕(我覺得好像永世那麼久)。然後是個盛大的游行,這游行我並不是頂喜歡。我寧願安步當車,享受鄉下景物。這時節,正值芽萌葉出,到處涌現新鮮的自然美。 在諾布林卡的消遣是數不盡的。諾布林卡有座高牆環繞的美麗花園。里面有許多建築,僚屬居停其間。另有俗稱黃牆的內牆,除了達賴喇嘛及其家眷,某些喇嘛可以出入,他人一概禁止。內牆的另一邊還有好些建築,包括達賴喇嘛的私人居所,有一個照顧得很周到的花園環繞其間。 我愉悅地在花園地徜徉個把鐘頭,漫步美麗的花圃間,觀賞棲止其間的許多鳥獸。其間常見的,有一群馴服的麝香鹿;至少有六隻巨大的西藏獒犬(Dogkhyi)充當警犬,是一位北京人從古本寺送來的。還有一些山羊;一隻猴子;從蒙古買來的幾隻駱駝;二隻豹;一隻又老又沮喪的老虎(當然關在獸檻中);好幾隻鸚鵡;半打孔雀;幾隻鶴;一對金鵝;大約卅隻非常抑鬱的加拿大鵝,翅膀都剪過,飛不動,我為牠們甚覺惋惜。 有隻鸚鵡對我的服飾總管天津甚為友善。他習慣餵牠們豆子。牠在天津掌中啄食時,他每每撫摸牠的頭,鳥兒此際似乎進入忘我之境。我非常想要這種友善的情誼,好幾次嘗試,希望得到相同的反應,但是沒有效果。所以我拿了一根棒子處罰牠。可想而知,以後每當看到我,牠就飛走。這對如何交友是個很好的教訓;交朋友不能靠強迫驅使,宜用同情體恤。 林仁波切和猴子同樣有很好的交情,牠獨獨對他友善。他往往從口袋掏出東西餵牠。所以,猴子看到他走來,就急急跳過來,開始在他長袍褶層中翻找。 我跟魚交朋友的運氣,比較好一些。魚住在一口魚族甚繁的湖里。我往往站在湖邊呼叫牠們。如果牠們有反應,我以小片麵包及粑獎賞牠們。不過,牠們有不服從的傾向,有時還漠不相應。如果這種情形發生,我大為震怒,不僅不給牠們食物,反而報之以石頭彈雨。不過,碰到他們靠近來,我會小心觀察小魚是否吃得到食物;必要時,用一根棒子把大魚趕開。 有一次,我正在湖邊戲耍,我看到一盞木燈飄近湖岸。我於是用撥魚棒試著撈起它。但是,緊接著我發現自己躺在草地上看星星。我掉進湖里,差點淹死。幸好我的一位從西藏西部來的潔役人員,以前當過兵的,一直注意我的舉動,所以一見情形不對,立刻跑來搭救。 諾布林卡宮另一個吸引我的是,奇處河(現名拉薩河)的一條支流就在附近,出了外牆,只要幾分鐘步程。小時候,我經常徵服外出,由一位侍從陪伴,走到奇處河邊。起初沒人注意;但是,到後來,塔湯仁波切下了禁令。不幸的是,達賴喇嘛所受規範十分嚴格。我被迫藏身內院,像一隻貓頭鷹。實際上,當時藏人社會甚是保守,連政府高級部長上街,都被視為不當,在諾布林卡宮,如同在布達拉宮,我大部分時間都和潔役人員一起。即使在很幼嫩的年紀,我已很討厭禮儀和形式,喜歡和僕從為伍,遠甚於政府官員相伴。 我尤其喜歡與我雙親的僕從為伴,每回只要回到故居,我總和他們耗在一起。他們大多是安多人,我很喜歡聽他們說起有關家鄉與鄰近地區的故事。我也很喜歡和他們一起『偷襲』雙親的存糧。 在這樣的場合,顯然他們也樂於有我為伴﹕這是一項互利的舉動。掠奪的最好時機是秋天,我們用紅番椒汁泡美味幹肉,貨源不絕。我愛吃極了,有一回吃太撐,隨即大吃苦頭。我俯身痛苦地乾嘔,天津瞧見了,適時給我一些鼓勵,比如說『這就對了,全吐出來。這樣對你比較好』。我覺得自己很驢,對他的關注也沒領情。 儘管我是達賴喇嘛,除非在正式場合,父母家的僕人卻視我一般小男孩。我沒被特殊看待,大家都敢把他們的悄悄話告訴我。因此,我很小的時候就明白,藏人生活並非日日平順。我的潔役人員也同樣放心告訴我他們的故事,以及在官員及高僧手裡遭到的不公不義。他們也讓我接觸到種種閒話雜談,通常是以歌曲或謠諺的形式表達,他們邊工作邊唱。所以儘管我的童年有時十分孤單,十二歲左右塔湯仁波切就禁止我再到父母家,但這種情形與悉達多王子或中國末代皇帝溥儀的情況完全不同。此外,我年級漸長之際,也接觸一些有趣的人。 實際上,在我整個童年時代,大約有十名歐洲人住在拉薩。我並不太常看到他們,直到桑天帶哈勒(Heinrich Harrer)與我見面,我才有機會了解英吉(inji)是什麼。藏人皆如此稱呼西方人(也許是因為藏人在十九世紀與印度的英國官員接觸,遂以此總稱西方人)。 我長大後,這些定居在拉薩的西方人中,包括英國貿易使節團委員長勾得爵士(SirBasil Goald)及其繼任者理查森(Hugh Richardson)。後者日後寫了好些有關西藏的書;而自從我出亡後,亦與他有過幾回頗有裨益的請益討論。除了福斯以外,還有一位英國醫官,我記不得他的名字。不過,我永遠忘不了有一回他奉召到諾布林卡,為一隻眼底長包囊的孔雀療傷。我看到他小心翼翼地,同時很訝異地聽到他以鼓舞的口吻,兼用拉薩方言和西藏敬語,對孔雀說話(而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語言)。而當這位外國人稱這隻鳥為『孔雀陛下』時,更讓我覺得此事非比尋常。 奧地利人哈勒擁有一頭我從未見過的金髮,確實是位可人兒。我暱稱他為『Gopse』,意即『黃頭』。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已在印度的英國監獄中,拘留了五年。但是,他設法和一位名叫奧夫秀乃特(Peter Aufschnaiter)的囚伴聯手越獄。他們一起逃向拉薩。由于西藏明令禁止所有外國人入內,除非少數獲得特殊允許者,所以,他們能到西藏,是項了不起的成就。在終於如願居留拉薩前,約有五年的時間,他們過著游牧式的流浪生活。他們抵達時,人們對他們的勇敢與堅持(以致官方同意他們居留),印象深刻。我當然是第一批知道他們抵達的人,非常熱切地想看他們的長相;特別是哈勒,他已在極短時間內,建立起自己的聲名;一位有趣的、擅交際的可人兒。 他能說一口極溜的西藏土話,還有絕妙的幽默感,兼之對人敬重又有禮帽。等我和他混熟後,他拋棄虛文,覺得十分坦率,除了有官員出席的場合以外。這是一種我極珍視的性情。 我們在一九四八年初見,在他離藏前的一年半裡,我們定期見面,通常是一星期一次。我能從他哪裡得知外界的狀況,特別是有關歐洲及世界大戰的種種。他也幫助我提昇英文程度,我才開始和一位政府官員學習英文。我早就認識字母,還曾把它譯成藏文語音,渴望學得更多。哈勒也在許多實際的方面協助我。 比如,他幫我修好發電機,那是隨著電動電影放映機附贈給我的。後來發現那部機器非常老舊,而且有毛病。我常懷疑是否英國官員沒把原要送的發電機給我,而把他們自己用過的給我? 這斷時期,我另一項關切對象就是達賴十三世進口的三部車。雖然西藏沒有適用的道路,直到他死前,他仍偶爾用車,作為行進拉薩市內及四周的交通工具。其中一輛是美國道奇車(Dodge);其它兩輛都是奧斯汀小車(BabyAustins)。三輛均是一九二○年代晚期的車型。還有一部威利牌的(Willy's)吉普車,這是由西藏貿易使節團一九四八年旅美推銷時所得的,但也很少用。 就像起先沒人會用電影放映機一樣,我也大費周章,才找到懂車子的人。不過,我決定該讓他們回到工作崗位上。最後找到另一位脾氣暴躁的司機泰塞林(TashiTsering),他是與印度接壤的南疆噶林邦(Kalimpong)地方的人。我們全力修復車子,甚至挪用另一部奧斯汀汽車的零件,我們終於修好一部車子。而道奇及吉普車情況較好,僅僅小規模地修補後,也能派上用場。 可以想見,一旦我們修好車子,我也只能在他們左近繞繞。但這對我已足夠了,有一天,得知司機不在,我決定開著其中一部車出外,道奇和吉普車都需鑰匙啟動,而鑰匙由司機保管。不過,小奧斯汀卻是用小型磁石發電機啟動,只需板動曲柄把手即可。 我小心翼翼地扳轉把手,把車倒出車庫,繼續在花園繞了一圈。不幸的是。諾布林卡宮的花園都是樹,沒多久我就撞到一棵樹。令我驚駭的是,我眼睜睜地看著一個車前燈的玻璃撞破了。除非我能在第一天之前修好,我的歡樂之行將會被我的司機識破,那可有麻煩了。 我著手把車子開回去,不敢再有絲毫差池,同時立刻試著修復破碎的玻璃。更讓我驚慌的是,我發現那不是普通的玻璃,而是彩色玻璃。所以,盡管我打算找到一塊足以搭配的玻璃,好好修補一番;我隨即又面對如何使新的玻璃與原有的玻璃拼湊的問題,這個問題終於以涂抹甜的巧克力糖漿綴連而解決。最後,我很中意自己的作品。即便如此,後來我見到司機時,仍滿懷罪惡感。我確信他一定知道,或至少也發現發生了怎麼一回事,但他從未提起,我永遠不會忘記他,他仍健在,如今住在印度,儘管我很少見到他,還是把他視為好友。 西藏的歷法相當複雜。它是以月亮的周期為基準,幾百年來,我們的歷法是以六十年為一周期(饒迥),這六十年是用五種元素、十二生肖來排列組合,五種元素是地、風、火、水、鐵,十二生肖是鼠、牛、虎、龍、蛇、馬、羊、猴、雞、狗、豬,依序配合計年,每一『計年』出現兩次,第一次是陽性,第二次是陰性,十年算完。然後五種元素又從生肖的第十一及十二起計數,再來則是從生肖的十三、十四起計算,依序類推。所以,比如西元二千年,根據藏歷則是鐵龍年。 先前數世紀,西藏遭中國侵略之前,一年裡有不少慶典節日,通常皆有宗教上的意義,不過僧俗同樣慶祝。後者皆將時間花在吃、喝、唱、舞及玩遊戲上,也有間歇性的祈願。最重要的年度活動之一是新年的活動,或稱羅薩節(Losar),時當西歷的二或三月。對我而言,這是我一年一度與國師涅沖(Nechubg)公開會面的時候。稍後章節,我會詳述;基本上這給我和政府透過靈媒(Kuten),針對來年事宜,諮詢西藏守護神扎滇金剛的機會。 我對某個慶典活動懷有非常複雜的情緒。此即緊跟著羅薩節之後的默朗木節(Monlam),即大祈願節,原因是我很小的時候,曾以達賴喇嘛的身分參加這個節日裡最重要的儀式。這個節日對我的另一項陰影是,我照例要忍受嚴重的熱症,就像我現在只要到印度菩提伽耶(Bodh Gaya),隨時都要發上一陣燒一樣。因此我在大昭寺時,多半都待在屋裡;儘管那個房間比我住在布達拉宮的房間更多塵垢。 這個令我悚栗非常的供養儀式(Puja)下午舉行,時值默朗木祈禱大會的頭一個星期的尾聲(全程二星期)。在一個由攝政王講釋迦牟尼佛生平的冗長講道後,供養儀式即持續四小時。然後,我必須憑記憶背誦一段又長又艱澀的經文。我緊張得腦裡一片空白。我的高級親教師即攝政、初級親教師、儀式總管、服飾總管以及掌膳總管都同樣為我擔憂。他們主要的憂慮是,典禮全程中,我都高踞法座,如果我忘詞,沒人能及時為我提示。 不過,記台詞只是問題的一半。因為典禮為時甚久,我有另一項恐懼:我怕膀胱負荷不了。最後,一切順暢;即使當時我還很小。但是,我記得曾因害怕而中風。我的意識麻木到無法察覺周遭一切的程度,連鴿子飛進來,偷吃供碟裡的食物,也不知道。只有在致辭的中途,我才注意到它們。 典禮結束,我高興得幾近恍惚。不僅是這整個討厭的活動十二個月後才會再舉行;而是現在接下來才是達賴喇嘛最美好的時光之一。典禮萬後,我獲准外出上街,觀賞巨大華麗的食子(Thorma,手捏的供品),這是當天照例用來供佛的。還有由軍樂隊表演的木偶戲和音樂,全民則陷入狂熱的歡樂氣圍中。 大昭寺是全藏最崇高的寺廟。是西元前七世紀,松贊乾布王統治期間建築的,以供奉他的妻子慈珍請回的佛像(她是尼泊爾國王布勒的女兒,松贊乾布共有四位妻子,三位是藏人,另一位是唐朝第二位皇帝唐太宗的女兒文成公主)。經過數世紀的修茸,大昭寺已再擴建,而且經過費心地妝點。矗立在入口的石碑是大昭寺的著名特色,上面銘記了西藏歷史諸多勢力消長的見證。碑銘以漢文與藏文並列,記載著西元821至822年唐朝與吐蕃簽定的永久和約的全文 ⑦ 。 我住在大昭寺的房間位於二樓,即是這座寺廟的平頂。我不僅能從這裡看到這幢建築本身的主體,還能看到底下的市場。往南開的窗戶,使我能綜覽主殿的景觀,我能看到和尚整日誦經不絕。他們總是表現良好,勤勉從事。 不過,從東邊的窗戶看出去卻是迥然不同的景象。我能俯瞰庭院,那是像我這樣的沙彌集合的地方。我往往很驚訝地看到他們逃學,甚至偶爾相互大打出手的場景。我還小時,總是匐匍下樓,以便取得一個觀察他們的較佳視角。我簡直不敢相信我的聞見。一開始,他們並未循規蹈矩唱誦經文。如果他們懶得大張其口,至少會吟唱。不過,相當多數似乎從未如此做,反而全把時間耗在嬉游上。一場混戰經常隨時開打。然後他們拿出木缽,互相重擊頭部。這個場景引發了我的一個奇特反應。一方面,我告訴自己這些傢伙有夠笨。另一方面,我卻忍不住羨慕他們,他們似乎與凡俗無涉,不過,當他們的爭戰轉趨暴烈時, 我開始覺得害怕,就跑掉了。 從西邊望出去,我能看到市場。這是個很易得我歡心的角度;不過,我必須秘密地窺視,而非光明正大地觀看,以免有人認出我來。如果有人看到我了,每個人都會跑過來,向我行五體投地的大禮拜禮。所以,我僅能透過窗簾窺探,感覺像個罪犯。記得大約七、八歲,我來到大昭寺的頭一回或第二回,我曾經做過一些嚴重玷辱自己的行為。一看到底下囂攘的人群,對我來說,實在是太多了一些。我粗魯地用頭戳破窗簾,但是,如果只是這樣,倒還好;糟的是,就在老遠底下,有人行大禮拜禮時,我居然吐了唾液星沫,落在好幾個人的頭上。 從此以後, 我可以欣慰地說,年輕的達賴喇嘛終於學到一些自我訓練的課題。 我喜歡窺視市場攤商百態,記得有一次看到一支木製的模型小槍。我遣人去買回來,然後從信徒供奉的獻金裡,取出一部分支應。我偶爾動支這部分的獻金濟急,因為我並未明文獲准處理金錢。事實上,甚至一直到今天,我還是沒有直接經手過錢。所有我的收入以及開支是由我的私人辦公室處理。 待在大昭寺的另一件趣事是,有機會和那裡的潔役交朋友。如同以往,我所有餘暇都與他們為伴,我也相信我離去時,他們也會和我一樣難過。記得有一年,在先前的慶典期間,我已與他們建立穩固的交情,而他們卻不在留在那裡。我納悶為什麽,因為我非常渴盼再見他們一面。我向唯一留下來的人詢問,想要知道到底是怎麽一回事。他告訴我,其餘十個人全因竊行遭解僱。我上回離開後,他們爬下天窗,闖入我的房間,竊走各種物件、金制酥油燈等等。我交的這種朋友,多過分! 默朗木大會的最後一天,是戶外活動的天下。首先,由一尊大的當來下生佛彌勒菩薩雕像前導繞境。這條路線就是昔日知名的外廓(Lingkhor)。聽說這條古道因為漢人拓城而不復存在。但是,緊繞著大昭寺開展的內廓(Barkhor)仍然存在。以前,虔誠的朝聖者更是沿著外廓,一路行五體投地的大禮拜。 就在佛像繞道完畢不久,眾人把注意力轉向體育活動,引起一陣全面的騷動。包括賽馬及賽跑,趣味橫生。前者更屬罕見,因為沒有騎士控禦。它們皆在哲蚌寺外獲釋,然後馬夫及旁觀者引導到市中心。就在馬匹抵達之前,那些競逐賽跑的準運動員也才出發一小段路程,目的地亦為市中心。因此當人與馬同時抵達時,可能會造成一種有趣的混亂場面。不過,有一年發生一件不幸的意外,就在部分選手急抓住路過奔馬的尾巴之際,卻被拽著跑。賽跑隨即結束,侍從長指控那些他認為可能涉嫌的人。他們大多數是我的侍衛隊成員。當我得知他們可能遭受處罰,心中非常難過。最後,我一度為了他們,而介入調停。 默朗木大會的某些方面密切地影響拉薩的所有人。根據古來傳統,大會期間(正月初三至廿五日),市政交由哲蚌寺稚巴(相當於漢地的方丈,但地位不同)掌理。他隨即從寺中喇嘛任命一個維持法律和秩序的幕僚團和警紀團。嚴格執法,任何不軌的行為皆處以十分嚴重的處罰。其中哲蚌寺稚巴始終堅持的就是清潔問題。結果,一年中就是這段時間每幢建築都洗刷鮮明,街道也徹底清掃乾淨。 孩提時,新年期間有件重大事情,那就是傳統烘焙的卡塞或羅薩餅乾。每年默朗木慶典期間,我的掌膳總管會做許多爐造型奇特、烤的焦香的美味點心。有一年,我決定親手試做一些點心。一切進行順利,我對自己的手藝也十分感動,所以我告訴掌膳總管,明天還要多做一些。 不幸的是,我第二回合用的油是未經適當處理過的生油。所以,當我把和好的麵團丟進鍋裡,油爆起如火山。我右臂濺滿熱油,立刻起了水泡。我對這件意外印象較深刻的是,有個年長的廚子,他愛吸鼻煙,滿鎮定的,當時他帶著看來像是攪成泡沫的油霜飛跑過來,敷在我臂上。平常他是個十分和氣的人,但在這種場合,他變得格外慌亂。我記得他邊吸少許鼻煙,邊流鼻水,滿怖痘癜的臉上卻掛著一副嚴肅的表情,想到那副樣子,實在滑稽。 所有節慶中,我最喜歡的是長達一周的藏劇節,每年的七月初一開鑼。由來自全藏各地隸屬不同團體的舞者、歌者及演員登場。他們在一塊距離黃牆若遠實近的特定區域表演。緊鄰牆內的一幢大樓頂端上豎上臨時的圍場,我就坐在那裡觀賞節目。其他的觀賞者都是政府官員以及他們的妻眷-她們視此場合為與他人比美珠寶與衣飾的最好機會。不過,這種情形不僅限於女士。這也是諾布林卡宮的潔役雀躍的時刻。在慶典節日的前些日子,他們即大費周章地租借衣服和珠寶,尤其是珊瑚,以便炫示。慶典期間舉行的園藝比賽,就是他們嶄露頭角的時刻。那時,他們攜著器皿(燒過的瓶子),裡頭長滿等待品評的花兒。 我永遠忘不了我的一位潔役,他總是戴著一頂奇特的帽子露面,他頗以那頂帽子為傲。那頂帽子綴有紅絲長流蘇,他別出心裁地讓流蘇繞過他的脖子,垂在肩膀上。 群眾也來觀劇,雖然他們不是政府官員或貴族,無法得到特別座的待遇。正如乍睹表演,民眾也對達官貴人們華麗的慶典禮服感到驚異目眩。他們往往趁機手持祈願輪,巡行黃牆的周界(祈願輪包括一個內有祈禱文的圓筒,當信徒口誦咒語時,即滾動之)。 除了拉薩人以外,許多來訪的民眾都很高大,有來自東方,虛張聲勢的康巴人,他們的長髮辮奢侈地綴以紅流蘇;從南方來的尼泊爾及錫金商人;當然還有矮小的、骨瘦如柴的游牧農人。人們縱情享樂,事實上,藏人天性即精於此道。我們絕大多數是單純的人,喜歡的也不過是一場好的表演和聚會,儘管不合法,仍有許多僧院人士參加,因此都要化妝與會。 多麽快樂的時光!在表演進行中,人們並坐交談,他們對歌與舞如此熟稔,所以他們了然每一個情節。幾乎每一個人都攜來野餐、茶和青稞釀的啤酒,來去自如,年輕的婦女袒胸哺乳,孩童咯咯笑著來回奔跑,只有在佩戴著絢麗斑斕妝扮的新表演者上場時,他們才會瞪大眼睛,直勾勾地看數秒鐘。而此刻,獨坐老叟木然的臉上表情也會綻放光彩,老嫗也會暫時停止閒話。然後一切又如常。而陽光不斷穿透稀薄、清新的山中空氣灑落。 可以確定的是,只有在諷刺劇上演的時候,大家才會聚集焦點。演員妝扮成比丘和比丘尼、高官以及國之祭師的模樣,以嘲諷之詩文諷喻公共人物。 其他一年中的重要活動,包括三月八日的大黑天節(Mahakala)。夏天堂堂揭始,當天所有的政府官員都要換夏裝。這天也是我從布達拉宮移駕---到諾布林卡宮的日子。五月十五日是普願節(Iamling Chisang),這個節日代表長達一星期的假期開始了。大多數的西藏人,不論僧、尼或政府官員都到拉薩外的平原露營,舉行一系列的野宴,以及其他的社交娛樂活動。實際上,我相當肯定有些人即便不打算出席,也會以化妝形式出現。然後是十月廿日的燃燈節。這是紀念西藏佛教的偉大改革者及噶魯巴(Gelugpa)教派創教人宗喀巴圓寂的忌辰。包括燃燈遊行以及點燃全城數不清的酥油燈。這天也是冬天伊始的日子,官員換上冬服,而我也不情願地回到布達拉宮。我渴望長大,以遵循我前世參加遊行的例規,然後回到他深愛的諾布林卡宮。 還有許多純粹世俗化的活動,在一年裡的不同時節舉行。比如正月舉行的馬展。秋天,也同樣是一年裡的特殊時段,此時,游牧人牽來犁牛賣給屠夫。此際令我神傷。我忍不住想到這些可憐的傢伙,就都要死了。只要我看見諾布林卡宮後的動物被送給市場待宰,我總是派人以我的名義設法買下,如此,我就能救們的命。經年以來,我想我大概已經救了至少以萬計的生靈,或許是更多。當我思及此,我想這個調皮透頂的孩子畢竟做了一些好事。 譯註: ① 仁波切舊譯為熱振呼圖克圖。 ② 各種貼身侍從,舊譯分別為其巧堪布:總堪布,管理達賴私人印信。森堪布:隨侍起居。蘇堪布:掌管飲食盥洗。卻堪布:掌管誦經、禮拜、供養。 ③ 維美是普通書信和其他通俗文件中所用的草體,又稱『五頭體』。烏千是正楷或『有頭體』,用於教授、書本印刷等。 ④ 即五明和五大部。五明包括內、因、工巧、醫、聲明;五大部包括現觀莊嚴論、律經、俱舍論、入中論、釋量論。 ⑤ 又稱小五明。即修辭學、詞藻學、韻律學、戲劇學、星相學。 ⑥ 音譯為『稱廈』,意即文學侍從或侍讀,有時候代替達賴喇嘛回答一些義理上的問題。 ⑦ 唐中宗建中二年,金城公主為敦睦兩國和好,上表請立碑銘,永社糾紛詔允之,今日拉薩大昭寺前,尚有唐藩甥舅聯盟碑文,屹立寺前。原文如下: 『唐有天下,恢奄禹跡,舟車所至,莫不率俾,以累聖重光,歷年惟永,彰王者之丕業,被四海之聲教,與吐蕃贊普,代為婚姻,固結鄰好,安危同體,舅甥二國,將二百年,其間或因小岔,棄惠為讎,封疆騷然,靡有寧歲,皇帝踐阼,愍茲黎元,俾釋俘隸,以歸蕃洛,蕃國展禮,同茲葉和,行人往復,累布成命,是必詐謀不起,兵車不用矣,彼猶以兩國之要求之永久,古有結盟,今請用之,國家務息邊人,外其故地,棄利蹈義,堅盟從約,今國家所守界涇州西,至彈箏峽西口,隴州西,至清水縣,鳳州西,至同谷縣暨劍南西山,大渡河東,為漢界,蕃國守鎮在蘭,渭、原、會、西至臨洮,東至成州,抵劍南,西界摩些諸蠻,大渡河西南,為蕃界,其兵馬鎮守之處,州縣見有居人,彼此兩邊,見屬漢諸蠻,以今所分,見住處依前為定,其黃河以北,從故新泉軍,直北至大磧,直南至賀蘭山駱駝嶺為界,中間悉為閒田,盟文有所不載者,蕃有兵馬處蕃守,漢有兵馬處漢守,並依見守,不得侵越,其現未有兵馬處,不得新置,並築城堡耕種,今二國將相,受辭而會,齊戒將事,告天地山川之神,惟神照臨,無得愆墜,其盟文藏於宗廟副在有司,二國之成其永保之。 』 |
| © The Office of His Holiness the 14th Dalai Lama. e-mail: service@dalailamaworld.co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