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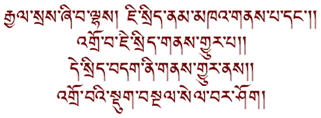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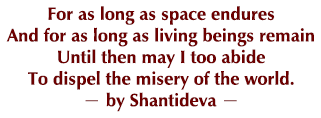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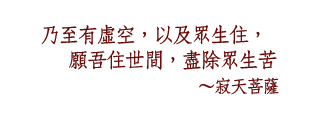 達賴喇嘛格言
快樂的人通常都有兩個特質,一個是他們很樂於給予,一個是他們容易寬恕。
相關連結
|
藏曆:2152 木蛇年
⌘ 流亡中的自在 ⌘
第一章:手持白蓮的觀音
一九五九年三月,我逃出西藏,從此以後,一直流亡印度。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年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兵入藏。將近十年,我身兼政教領袖,致力重建兩國之間的和平關係,但是終歸無效。我得到令人傷感的結論﹕我在西藏外面,能對留在西藏的人民做出更大的貢獻。
當我回顧西藏還是自由國度的時光,發覺那是我一生中的黃金歲月。今天,我的確是快樂。但面臨的現況無可避免的迥異於從前我成長的時代。儘管沉緬於懷鄉思緒顯然無益,每當憶及過往,我仍不禁神傷,我想起同胞遭逢的非常苦難。古老的西藏並不完美,然而,實不相瞞,當時藏人的生活方式確是獨樹一格,有很多的確值得保留,如今卻是永遠失傳了。 我說過,「達賴喇嘛」一辭意涵言人人殊;但對我而言,此辭僅關涉到我的職務。實際上,「達賴」是個蒙古字,意即「海洋」;而「喇嘛」是個相當於印度字 Guru 的藏文,意指上師。「達賴」與「喇嘛」兩個字合起來,有時被泛解為「智慧之海」。但是,我認為這是出於誤解。「達賴」只是「索南嘉措」(Sonam Gyatso)--第三世達賴喇嘛名字的部分意譯。「嘉措」意即藏文裡的海。更嚴重的誤解自中國人把「喇嘛」解為「活佛」,意喻「活著的佛」。這是不對的,西藏佛教裡沒有這回事。只有這種說法:某些人可以自在地轉生,例如達賴喇嘛,這種人稱為「化身」(tulkus)。 當我還駐錫西藏,身為達賴喇嘛,象微著人間天上。它意味著過著一種遠離絕大多數人民塵勞、困頓的生活。我到任何地方,都有侍從相隨。我被裹著華麗絲袍的閣員及長老們圍繞,這些人皆從當地最高尚、貴族的家族擢拔而出。每天與我相伴的,則是睿智的經學家及充分嫻熟宗教事務的轉家。每回我離開布達拉宮--有一千個房間的狀麗冬官,總有數以百計的人群列隊護送。 隊伍的前頭是一名拿著「生死輪迴」象微的男子(Ngagpa),他後面是一隊帶著旗子、著五彩斑斕古裝的騎土(Tatara)。其後則是挑夫,攜著我的嗚禽籠子及全用黃絲包裹的個人用品。緊接著是來自達賴喇嘛本寺南嘉寺的一群和尚,他們都拿著飾以經文的旗幟。隨後則是騎著馬的樂師。再後,跟著兩群僧官,首先是低階和尚,他們是抬轎的;然後是澈炯階級的喇嘛(Tsedrung)①,他們都是政府官員。達賴喇嘛廄中的馬群英姿矯健地跟在後面,皆由馬夫控馭,並飾以馬衣。 另一陣馬群則馱著國璽。我則隨後坐在由廿名男丁抬著的黃轎裡,他們都是綠衣紅頂的軍官。與大多數高級官員不同的是,他們有自己的髮式,留著一條長辮子,拖在背後。至於黃轎(黃色指涉修行意涵)則由另外著黃絲長袍的男子扛抬。轎旁,四名達賴喇嘛核心內閣成員噶廈(Kashag)② 騎馬緊隨,由達賴的侍衛總管(Kusun Depon)及西藏軍總統領馬契(Makchi)照應。行伍皆佩劍凜然致敬,他們著藍褲和飾以金色穗帶黃束衣的制服。頭上則戴著流蘇帽。隊伍四周,最主要的團體是一群警衛僧(singgha)。他們看來聲勢懾人,一概至少六呎高,穿著笨重的鞋子,平添外表的奪目之感。他們手裡拿著長鞭,隨時派上用場。 我的轎後是高級及初級親教教師(前者是我即位前的西藏攝政)。然後是我的父母及其他家人。接著是包括貴族及平民的一大群俗官,依階級出列。每當我出巡,幾乎所有拉薩人民都爭睹我的風采。所到之地,人們向我頂禮或五體投地,一陣令人敬畏的肅穆後,他們經常隨之涕下。 這種生活迥異於我幼年所過的生活。我生於一九三五年七月六日,名為拉木登珠,字面上的意思是「期盼充滿神性」。藏人為人、地、事命名,常取其傳神畢肖,比如,西藏最主要的河流之一,也是印度大川布拉馬普德拉河(Brahmaputra)源流的昌加波河(Tsangypo),其意即為淨化。再如我們居住的村莊塔澤(Taktser,位於今青海湟中祈家川),名為「咆哮之虎」。這裡是小而貧瘠的墾殖地,雄踞一座小丘上,俯視著寬闊的谷地。那片草地從未長期開墾或耕種,只有牧人放牧。原因是氣候變幻莫定,不適農耕。小時候,我家即為典例,全家廿多人在這裡過著看天吃飯的營生。 塔澤位於東北藏邊陲的安多省(Amdo)。在地理上,西藏可分為四個主要區域。北方是羌塘(Changthang)寒漠區,東西橫亙八百哩,幾是不毛之地,只有一些吃苦耐勞的遊牧人在荒煙中出沒。羌塘南邊是鳥昌省(U-Tsang)③。其南方及西南方毗鄰的是高大的喜馬拉雅山。鳥昌省東邊是康省(Kham,即中國的西康省),是全藏最肥腴的地方,因此人煙也最稠密。康省北方是安多省,兩省的東邊則是西藏與中國分界的天然屏障--高原縱谷。我出生時,一名回教軍閥馬步芳才剛在安多建立了一個效忠於中華民國的地方政權。 我的雙親是小農,不完全是農夫,因為他們從未與任何地主有所關連;但他們絕非貴族階級。他們擁有小塊土地,自力耕種,西藏主要農作物是青稞和蕎麥。家父母兩者都種,還有馬鈴薯。但是,他們終年辛勤,常因嚴重的降雹或乾旱而付諸流水。他們也養些牲口,這是比較靠得住的生產資源。我記得我們有五或六隻擠奶用的(此字不在電腦中,左邊一個“牛”字,右邊一個“扁”字)牛(dzomos),這是犛牛與水牛的雜交種,以及一些生蛋用的土雞,還混養了一群大約八十頭的綿羊和山羊。父親愛馬,幾乎總有一兩匹甚或三四匹馬。此外,我家有一對犛牛。 犛牛是上蒼賜於人類的一種禮物。牠能存活在一千呎以上的高地,所以極適應西藏。在低於千呎以下,則很難存活。作為負重的牲口以及奶(母犛牛才能擠奶,稱為dri)、肉的來源,犛牛真是高原農作的一寶。雙親種的青稞則是西藏的另一寶。將青稞焙乾,研磨成細粉,即成糌粑。在西藏,很少有一餐不用到糌粑,即使在流亡生涯,我仍然每天吃糌粑。當然,我們並不光吃麵粉;首先必須與液體攪拌,通常用茶,但牛奶(我喜歡)或牛奶提煉的半個態酪(yoghurt),甚至青稞釀成的啤酒(chang)也可以。然後用手指在碗底攪和,捲成小球狀。否則,也可以煮成麥片粥。西藏人非常喜歡這樣的美味,雖然在我經驗中,少有外國人敢領教。中國人尤其是一點也不喜歡。 雙親種的大多數作物只用來養我們。父親偶與過路的牧人交換殼物或綿羊。他間或下山到最近的城市西寧—安多省的首府,從事交易,騎馬需時三個鐘頭。在這廣袤的鄉區,貨幣並不太流通,大多數交易仍是以物易物。因此父親可以把當季收成盈餘交換茶、糖、棉布,也許是一些裝飾品以及一些鐵製用品。有時帶回一匹新的馬。他可樂了。他很善待這些動物,並以善治馬疾享譽桑梓。 我誕生於一座典型的藏人住屋裡,屋子以石塊與泥造成,圍住一個廣場的三面。它唯一特色是杜松木做成的水槽,鑿成半圓形狀,以利雨水宣洩。在它的正前方兩翼之間,有個小天井,立著一根長竿。旗竿上掛著一面祈禱幡,頂部及底部繫緊,上面寫著數不清的祈禱文。 牲畜養在屋後。屋裡有六間房,其一是廚房,在室內時,我們在廚房消磨的時間最多;一間有座小佛壇的祈願室,每天清晨,我們都得群集在此獻供;雙親的臥室、客房、食物儲藏室,以及牛棚。我們小孩沒有臥房。在嬰兒期,我與母親睡;稍大時,睡在廚房的火爐旁。至於家具,沒有我們一般所謂的椅子或床,但在雙親臥房及客房裡,有凸起的睡眠區域。屋裡還有很多華麗的漆畫木製小櫥。地板同樣是木製,是平整鋪成的厚板。 我父親中等身材,急性子,我記得有一次我扯了他的鬍子,因為頑皮,被狠揍了一頓。不過,他仍是一位慈悲的人,從未心懷不滿。聽說,我出生時,他有件趣事。他病了好幾星期,不能下床。大家都不知道是什麼病,開始擔心他性命不保。但就在我出生當天,他突然毫無來由地逐漸康復。再為人父,並無欣喜,因為家母已生了八個小孩,其中僅有四個存活(像我們這樣龐大的農耕家族的确有必要多生小孩,家母共生了十六個,其中七個活下來了)。撰寫本書時,我上面的哥哥羅桑桑天(Lobsang Samten)以及大姐澤仁多瑪(Tsering Dolma)已辭世。但我另二位哥哥、妹妹及弟弟仍安然健在。 家母無疑是我見過最慈悲的人之一。她真是好得不得了,我确信所有認識她的人都喜歡她。她非常有同情心。有一次,記得有人告訴我鄰近的中國發生可怕的饑荒。結果,許多可憐的中國人越界覓食。有一天,一對夫妻出現在我家門口,懷中抱著死去的孩子。他們向家母乞食,母親欣然給予。然後她指著他們的孩子,問是否需要幫忙埋葬。當他們明白家母的意思,於是搖頭,並澄清說打算吃掉『它』。母親嚇壞了,立刻邀他們入屋,出清儲藏室的全部食物,然後傷感地送他們上路。即使這樣布施家用食物,意味著我們自己可能要挨餓,她仍從未讓乞丐空手而歸。 多瑪是家里最大的孩子,長我十八歲。早在我出生前,她就很盡心協助母親管理家務。她是我出生時的接生婆。她接生我時,發現我一隻眼睛張得不夠開,毫不猶豫地把她的拇指放在這隻不聽話的眼皮上,強行把它打開,幸運的是,沒有留下不良的後遺症。她也負責供應我的人間第一餐,傳統上,是取自當地產的一種特殊灌木皮的液體,大家相信如此可保證孩子健康。當然我也得如法炮製,幾年以後,姐姐告訴我,我是個非常髒的嬰兒。她剛把我抱到懷里,我就拉了一堆屎。 我跟三位兄長都沒有什麼相處。大哥圖登吉美諾布(Thupten Jigme Nopbu)早被認定為高級喇嘛塔澤仁波切(Taktser Rinpoche, 仁波切是賦予精神領袖的頭銜,其字面上的意義是『寶』的化身,而被迎請到離家好幾小時馬程的著名大寺——告本寺 ④。二哥嘉洛通篤(Gyalo Thondup)長我八歲,我出生時,他早已到鄰村就學。只有長我三歲的三哥羅桑桑天留在家里。但他後來也到古本寺出家,所以在家時,我並不太了解他。 當然,除了看我是個普通的娃兒,沒人想到我可能會成為什麼。幾乎難以置信,一位以上的化身會降生在同一個家族。我的雙親當然也沒想到我會被認證為達賴喇嘛。父親的病癒是吉兆,但大家都不認為有什麼重大意義。我自己對前程同樣沒有特別的暗示。我最早的記憶非常尋常。有些人非常強調人們的最初回憶,我則不然。比如,我記憶中,發現一群孩子打架,我立刻加入弱者的一邊。我也記得首次看見駱駝。駱駝在蒙古地區非常普遍,但偶爾會穿越接壤處。身形龐大、壯觀的駱駝,看來非常駭人。我也想起有天發現我染了東藏習見的寄生蟲病。我記得,我很小的時候特別喜歡做的一件事,是隨母親到母雞窩里撿蛋,然後落在後面,坐在母雞孵蛋的巢上,學著母雞呼雛咯咯叫。孩提時,另一件令我雀躍的事是,假裝即將出遠門,收拾物件放進袋子里,然後說,『我要到拉薩了,我要到拉薩了』。還有,我總是堅持坐在桌子的上座,後來被認為是我必然知道命定要做更大事業的暗示。幼年,我也曾做過許多夢,都得到類似的解釋,但我始終無法直言知道自己的未來。後來,母親告訴我好些能喻義高僧轉世徵兆的故事。比如,除了母親,我從不允許任何人動我的缽。我也從未顯現怯生生的樣子。 在我繼續說到被尋訪、認證為達賴喇嘛轉世之前,首先必須說明佛教及其在藏地發展的歷史。佛教的創始者是位歷史人物悉達多(Siddhartha),後來他成了釋迦牟尼佛,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出現。他的教義在西元四世紀間引介入藏。他們費了好幾百年排擠土著本教(Bon),然後全面建立佛教信仰;舉國終於徹底改變信仰,因為佛教教義統御了整個社會的各階層。不過,藏人本質上是十分富侵略性的民族,相當好戰;然而,他們對宗教事務的興趣日增,是促使藏區遺世孤立的主要要原因。在此之前,西藏統領一個支配中亞的龐大帝國,疆域涵蓋北印度大部分區域、尼泊爾及不丹南部,也包括許多中國的領土。西元七六三年,藏軍確實攻佔了大唐的首都,得到對方輸貢的允諾以及其它的讓步 ⑤。不過,由於藏人日益耽於佛教,她與鄰國的關係成為一種精神上,而非政治上的性質。她與中國的關係尤然,因此發展出一種『僧伽和施主』(Priest Patrony)的關係。清朝皇帝也是佛教徒,稱達賴喇嘛為『闡教王』(Kingof Expounding Buddhism)。佛教的基本法則是緣起或因果法則。簡言之,人所經歷的每件事皆源自起心動念,而後有了行為。念頭因此是行為和經驗的根本。這樣的理解源自佛教意識及輪迴的教理。 前者主張,因為『因』引致『果』,再接著成為另一個『果』的『因』,意識勢必接續不斷。念念遷流,剎那相續,蘊集經驗與印象。到肉身人滅的剎那,念頭持續不斷,人的意識包括所有過去經歷及印象的烙印,因此去向就跟著業力流轉。這就是『業』(Karma),意即『行為』。這就是意識跟著各人造作的業,隨後『轉世』於一個新的軀體——動物、人類或天人。 舉個簡單的例子,有人生平虐待動物,來生極易投胎為狗,受主人欺凌。同樣的,生平懿德善行,有助來生善報。 佛弟子更進一步相信,因為意識的本質是無自性的,卻避免無止盡的生、苦、死、轉世等生命無可避免的負擔,是可以做得到;但是,只有世緣牽縈的惡業已經消除,才有可能。到達此一境界,意識毫無疑問地首先會得到解脫,接著是達到無上的成佛境界(轉識成智)。然而,根據西藏傳統佛教的觀點,菩薩雖已證得佛果,解脫生死輪迴,菩薩將繼續乘願再來,致力利益眾生,直到眾生皆得解脫而後已。 以我自己為例,我被認證為西藏前十三世達賴喇嘛每一世的化身(第一世出生於西元一三五一年)。這些化身又是觀音菩薩的示現,具大慈悲的白蓮花的持有者,因此,我也被視為白觀音(Chenrezig)的示現,事實上,在傳繼系統里的第七十四代,即可溯及一位婆羅門(Brahmin)男孩,他是釋迦牟尼佛時代的人。常有人問我,是否真的相信這些。這個答案不容易回答,但如今我已五十六歲,檢視此世的經歷,以及以佛弟子的信念見證,我毫不遲疑地認定,我在精神上與先前十三世達賴喇嘛、白灌音及佛陀本人相應。 我還不滿三歲時,政府派出一個尋訪團,打探達賴喇嘛的新化身,他們被許多跡象引導,來到古本寺。其中一個跡象,與我的前生達賴喇嘛十三世圓登嘉措(Thupten Gyatso)有關,他在一九三三年五十七歲圓寂。在他涂了香料的遺蛻,趺坐接受瞻仰期間,發現他的頭從朝南轉向朝東北。緊接著,一位高級喇嘛——攝政本人,看到一幅觀境。他在藏南聖湖拉嫫拉措湖(Lhamoi Latso),清楚地看到水里三個藏文字母﹕Ah、Ka及Ma,浮現眼際。接著出現下列影象﹕一幢三層樓寺廟,有綠藍色與金色屋頂,以及一條到山上的小徑。最後,他看到一件有怪異造型導水糟的小房子。他確信Ah字母暗示安多(Amdo),在東北方,所以尋訪團就出發了。 抵達古本寺(拉薩至此,要三個月旅程)時,尋訪團成員覺得他們走對路了,看來如果Ah字母喻安多(Amdo)的話,Ka勢必喻義位於古本(Kumbum)的這座寺,而它也確實是三層樓,且有綠藍色屋頂。他們現在只須找出那座山及有特殊導水糟的房子。所以,他們開始尋訪附近的村落。他們看到我家屋頂上結瘤的杜松木幹,即確定轉世的達賴喇嘛就在左近。盡管如此,他們並未透露此行的目的,只要求過夜。尋訪團的領袖結昌仁波切(Kewtsqang Rinpoche)大半個晚上扮作僕人,與屋子裡最小的孩子玩耍,伺機觀察。 小孩認得他,大叫『色拉喇嘛,色拉喇嘛』,色拉(Sera)是結昌仁波切駐錫的寺。翌日,他們就走了,幾天後再回來,這次是正式的代表團。他們攜來許多我那位前世的個人用品,混雜了一些他沒有用過的相似物件。每天試驗,小孩總是正確無誤地認出達賴喇嘛十三世的用品,並說『這是我的,這是我的』。這些多少證實尋訪團已經找到達賴喇嘛的新化身。不過,在最後的結果揭曉前,還有另一位可能人選猶待驗證。但沒多久,這位塔澤男孩即被確認為新的達賴喇嘛,我就是那個小孩。 不用說,對這件事,我記得不多。我太小了。我只記得有個雙眼銳利的人。這人名叫天津(Keurap Teuzin),他成為服飾總管,後來教我寫字。尋訪團認定我就是達賴喇嘛的真正化身,消息傳回拉薩,報知攝政,在得到正式確認之前,還要好幾個月,這段時間,我仍待在家裡。其間,安多省地方政權的首長馬步芳開始找麻煩。但是,最後雙親把我帶到古本寺,我在那里升座,儀式在黎明舉行。我特別記得這件事,因為日出前我就被人猛然喚醒、更衣,我也記得坐在法座上。 於是從此開始了我生命中一段並不怎麼快意的日子。我父母並沒在那裡待太久,不久以後,我即孤零零置身於陌生的新環境,與父母生離,對一個小孩是一件頗殘酷的事。幸虧寺中生活還有兩事差堪告慰。其一是,我三哥桑天早上就在那裡,雖然只大我三歲,他把我照顧得很好,我們很快成為親密的朋友。第二件是,他的上師是位非常慈悲的老喇嘛,常把我藏在他袍子里。我記得有一回他給我一枚桃子。但大多數時候,我很不快樂,我無法理解成為達賴喇嘛意味著什麼。我只知道——我是許多小男孩之一。小小孩進寺並不稀奇,我也被一視同仁。比較痛苦的一件記憶和我的一位叔叔有關,他是古本寺的喇嘛。有一天傍晚,他正坐著讀祈禱文,我弄翻了他的書。正如今天所見,這本經典已書頁脫落。所以,當時我一碰即散。叔叔抓起我,狠狠揍了我。他非常憤怒,我也嚇壞了,之後的的确确有好幾年,我一直忘不了他黝黑的、麻瘢的臉、以及刺人的鬍子。從此以後,只要看到他,我就非常恐懼。 我得知能與雙親永遠團聚,要一起到拉薩,才開始覺得來日有些興味。就像一般的孩子,我對旅行的種種,興奮莫名。不過,此行耽擱八個月之久,因為馬步芳勒索巨額贖金,不讓我到拉薩。他嚐到甜頭,需索更多。直到一九三九年夏天,我到拉薩前,一直如此。 好日子終於在我四歲生日過後一星期到來。記得當時充塞一片樂觀之情。護送我回拉薩的隊伍非常浩大,不僅包括我雙親以及我三哥羅桑桑天,也包括尋訪團的成員以及許多朝聖者。同行的,還有好些政府官員以及大量馭騾者和斥堠。這些人終身僕僕西藏商旅路線之間,任何長途旅行都非借重他們不可。他們知道每一條河正確的渡河位置,也知道攀越一座隘口要多少時間。 經過幾天的旅程,我們離開了馬步芳的轄區,西藏官方正式宣布承認我為達賴喇嘛的新化身。現在,我們進入某些世界上最渺遠、最美麗的鄉道﹕巍峨的山嶺綿延著平坦的草原,我們如昆蟲般,奮力越過。偶爾會遇到融冰成水的河流湍急而下,我們潑辣地踩水而過。每隔幾天,我們會踫到一個小小的屯墾區,群擠在草原中的溝火旁,或者宛如附枝般,守著一片山坡。我們能遙見一所寺廟奇跡似地棲停在懸崖之上。但大多數時候,那裡只是乾燥不毛的空地,惟有挾沙的野風和狂亂的降雹,讓人知道大自然力量的可畏。 這趟到拉薩的旅程耗了三個月。我記得不多,只除了對所見每事的新奇感﹕龐大的野犛牛群奔越平野,一小群的野驢以及偶見的一陣閃光,小鹿輕捷,迅速鬼魅。我也愛時時可見的大群梟叫的野鵝。 大部分旅程,我都和桑天坐在由一對騾拉的車輿里。我們大半時間都在爭吵辯論,就如一般的孩子,甚至經常大打出手,如此使車輿經常陷入失衡的險境。此時,車夫就得制止這種『獸性』,請來母親。母親往內探看,總會看到同樣的景象﹕桑天流著眼淚,而我臉上掛著勝利的表情,安坐不動。因為,桑天年級雖然較長,我卻是比較直率的。儘管我們感情確實夠好,卻無法相安無事。我們之中,總有一個人會出言引發爭議,最後以打架和流淚收場;但流淚的總是他,而不是我。桑天就是脾氣太好,擺不出兄長的架勢來對待我。 最後,時序已入秋,我們一行人才接近拉薩。在我們距離拉薩還有數日行程時,出現一群政府高級官員,護送我們,直到離拉薩入口二哩外的多古塘平原。那裡早已樹立一座巨大的天幕營區。中間的一座是藍白結構叫做 Macha Chenmo 的『大孔雀』(Great Peacock)。在我眼中,異常龐大,它環繞著木雕的寶座,只是用來表達歡迎年幼的達賴喇嘛回家。 接下來的慶典持續了一天,授予我人民的精神領袖地位。關於此事,我的記憶很模糊,只記得歸家的盛大感覺,以及數不盡的人群。我永遠想不透那裡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總歸言之,整個過程我自認表現良好﹕年僅四歲的我,即使一兩位特別年長的喇嘛自行審度我是否為達賴十三世的真正化身時,亦泰然自若。然後,活動全部終了,我和三哥羅桑桑天被送往位於拉薩西方大約三公里的諾布林卡(意即珠寶邸園)。 平常,諾布林卡宮僅作為達賴喇嘛的夏宮。但是攝政決定等到明年底,才讓我在布達拉宮(西藏政府的所在地)正式升座。在這段期間,我必須住在那里。這實在是個很『英明』的決定,因為諾布林卡宮遠比布達拉宮好頑多了。諾布林卡宮由花園和許多小型建築組合圍繞,裡面風景清幽,空氣清新。布達拉宮則正好相反,我則見到塔樓壯觀地伸向遙遠的天際,宮裡則是黑暗、陰鬱的。 因之,我享有一整年不負任何責任的自由,快樂地與我兄長戲耍,並能定期回家看望父母。這是我所能擁有的最後的短暫自由。 譯註: ① 舊譯孜仲或濟仲,西藏政府之僧宮。 ② 噶廈類似內閣,成員有四位,清氏三名為俗家,一名為僧官。 ③ 烏昌舊譯為衛藏。 ④ 古本寺,藏語全名為『袞本賢巴林』,意為十萬獅子吼佛像的彌勒寺,一般漢譯其名為『塔爾寺』,是藏傳佛教善規派的六大寺院之一(餘五寺為西藏甘丹寺、哲蚌寺、扎什倫布寺、色拉寺和甘肅的拉卜愣寺)。塔爾寺也是黃教創始人宗喀巴大師的誕生地。 ⑤ 《資治通鑑》卷一二一三,唐紀三十九,代宗廣德元年戊寅年;吐蕃入侵長安,高暉與吐蕃大將馬重英等,立故邠王守禮之子承武為帝,改元置飛百官。郭子儀免胄見回紇是西元七六五年的事,唐與回紇聯兵破吐番。 |
| © The Office of His Holiness the 14th Dalai Lama. e-mail: service@dalailamaworld.com |


